“梦里,我化作一只小小的蚕——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吐丝、吐丝、吐丝……直到吐出
最后的一根,生命便该悄然离去……”
很多年后,杨苡依然会想起小学时代的那条小绿蚕,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刻,是如何被遗留在校园里,孤独地面对着死亡的命运。她尝试着去拯救这条微不足道的小小生命,却被姐姐强行拖了回来。她只能面对这场注定的生离死别。
死,她并非没有经历过。父亲死时,她尚在襁褓,父亲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家人偶然提起的模糊印象。二姐死时,她又太小,那个瘦削、安静而美丽的少女,她还记得她把软软的手放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而二姐的死带来的更像是一场沉默悲剧在猝然高潮后的戛然而止——长房正妻娘请了一个道士来病人床前作法,乌烟瘴气的香烟中,一只黑色的公鸡咔嚓一声被折断脖子,鲜血喷溅而出,那只垂死挣扎的公鸡一下子飞到二姐床前,这骇人的场面带给杨苡幼小心灵的,只有恐惧,当她回头看到二姐时,只见她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死亡带来遗忘,带来恐惧,也带来永别的哀伤。但校园里那条小绿蚕,让她理解了悲悯与爱,也让她感受到何谓离别。就在她行将离开那座教给她爱与离别的学校之时,她与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相遇了。他就是巴金。
别
她给巴金写第一封信时,十七岁。
在此之前,她已经读过了许多巴金的书。尽管杨苡自始至终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巴金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她一样捧来阅读。一如杨苡所感受到的,巴金的小说对“五四”后的年轻一代有独特吸引力,他的成名作《家》具有双重的魅力,既勾勒出一个衰朽旧式家族种种不堪为人所道的琐细暗面,足以满足那些窥探的眼睛,同时,书中塑造的三个主要角色:觉新、觉民、觉慧,更以他们的挣扎与奋争戳中了无数读者的心——毕竟,能够阅读并读懂这部厚重巨著的读者,大都也出自这样的旧式家庭,感受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旧雨新风的鞭挞与吹拂,他们能感受到书中人物的彷徨与无奈,听懂他们的抱怨与控诉。
“巴金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诚然,同样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家庭,同样少年丧父,家境也同样走向衰落,而自己也像主角一样,在新式学校中接受到了平等自由的新思想,那种渴望走出家去的强烈冲动,以及对离开校园直面世界的兴奋与不安,一切都如书中的那个年轻的主角觉慧一样。在第一封表达崇拜的信收到回信之后,杨苡写了第二封信,讲述了自己对家庭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
但巴金的回信,却表示“不赞成”,劝勉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对一个渴望走出压抑沉闷的旧式家族、拥抱崭新世界的少女来说,这无异于一杯冰水,多年后,杨苡依然对巴金为何阻止她成为书中离家出走的觉慧感到些许困惑。
“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但当时的杨苡或许未必完全了解巴金更体贴入微的苦心,他并非不愿自己的读者冲破旧式家族的束缚,为寻求自由而出走,只是,他更深知出走将会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书中那个离家出走的觉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巴金自己的写照,他确实离开家庭,沿着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他付出的代价,却非小说结尾那样安稳的结局。他离开了李家,但他的大哥李尧枚却要独立支撑起整个家族,负担起弟弟离家闯荡的资费。新的理论让他愿意将自己的弟弟送出家门,去追寻新潮,但旧的家庭环境却要求他肩负起所有的重担。“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而这种方式,是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在当时所不能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兄弟间的友爱,让大哥代替巴金和三弟承担了来自家族的压力,但他叛逆的弟弟却不能悦纳他,哪怕他写信告诉巴金自己会自杀,巴金依然“不曾重视他的话”。直到1931年暮春时节,他终于自杀了。读到大哥的遗书,巴金才明白为了自己的反抗,大哥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
或许正是在杨苡的第二封信中,巴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不愿这个女孩儿复制自己当年的悲剧。而这位一向为年轻人设想的年轻作家,或许为这位年轻的女读者考虑得更深更远。毕竟,社会发展永远会落后于思潮前进的速度,尽管早在清末便提出了“女界革命”的口号,鼓励女性行动起来,冲破家庭的桎梏,去做理想中自我解放的“新女性”,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绝非靠一两句口号可以抹平。
杨苡的四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杨苡父亲二姨太的女儿,当她离开杨家后,她同时也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京戏演员。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上午打了胎,晚上又要登台。“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杨苡如果离家出走,会不会像四姐一样,走上悲剧的绝境,或许难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家庭,都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巴金深深地明了这个道理,杨苡也很幸运遇到的这个愿意倾听她诉说的人是巴金。而更幸运的是,巴金推荐给她的另一位值得倾诉的对象,他的哥哥李尧林。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照片上的李尧林是个高而清瘦的中年人,在南开中学当老师。日军炸毁了南开学校的校舍后,他到耀华任教。比起巴金,大李先生更善于和年轻的学生们交往,“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他带给杨苡的,正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亲切、潇洒、衣着讲究得体,风度翩翩。他并非没有苦闷,但他在杨苡和朋友们面前总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消解苦闷,“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巴金是信纸那一端的师长,而大李先生则是一同散步、听音乐、看电影的身旁友人。大李先生写给自己的每一封信,杨苡都仔细地在信封背面下角写上数字,视若珍宝地珍藏起来。她心中定然对这位师长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多年后,她将这种情感解释为“敬仰”。但这种仰望中也包含着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与理解,是一种大大方方、干净澄澈的恋慕。就像当大李先生前往学校从杨家门前路过时,杨苡都会把房间里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是他们讨论过的音乐,“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
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一次电影散场后,大李先生默默地随着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地站在杨苡面前,“他没有喊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他。他笑起来,对她说: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是杨苡第一次来到海河边,尽管这里距离她居住在租界的家不过数里之遥,但她从未走到过这里。那一刻看到的一切,直到一个世纪后,依然清晰地铭印在她的脑海中。
“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大李先生轻轻地对她说。
“李先生,那你呢?”
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那天,杨苡在海河码头,登上了“云南号”客轮,离开天津。那天上午,他们想办法见了一面。李尧林送给她一盒贵重的手绢,他掏出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装满了碎纸片——那是她写给他的信,街道上空空荡荡,碎纸片抛撒漫天,纷纷扬扬。
她对他说:“昆明见!”
在她远离的那座房子里,他写给她的信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直到硝烟下战栗的火焰,将它们化为片片飞灰。
云
“月光像水一样洗着我们还湿着的头发,好像是在轻轻地梳着梳着,使它更显得乌黑浓密。那样清凉的月色拥抱着那样平静的海,仿佛它不久以前表现出的怒气全被月色温柔地抚平了,而顺从地展开了一幅无边的闪着银点的缎面。我们喃喃说:这多像梦!海之梦、月之梦,就这样任凭它载我们远行吧!是的,这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这般罗曼蒂克的海上梦幻,作为杨苡前往云南西南联大的铺垫,可谓恰如其分。西南联大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浪漫传奇。环境艰苦却名师林立,培育的英才更是各擅其才,在不同领域功绩卓著。杨苡前往的,正是这样一个神话般传奇的所在。恰如她在前往昆明的海轮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在晚年的回忆中,杨苡勾勒出的自己初见的昆明是宛若天津中西女校一般的世外桃源。她入学之初搬进的青云街8号,是一座云南样式典型的老式大院。尽管居住环境比天津租界的洋房要简陋不少,但对初来昆明求学的学子来说,却是燃烧着知识光焰的圣堂之一。她的左邻右舍皆是闻名遐迩的名人。与她同住第一进的郑颖荪是知名的古琴家。而住在后进的人则是沈从文与杨振声。给她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便是沈从文。这位和颜悦色的名作家,在得知她对文学诗歌的兴趣后,更乐于把她引荐给自己的文学同道,有天晚上,她“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沈从文特意朝她的窗户喊道:“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
杨苡也在西南联大收获了新的友谊,王树藏与陈蕴珍便是她的两个至交好友。王树藏是著名诗人萧乾的女友,萧乾亲昵地将她称为“小树叶”。而陈蕴珍,以“萧珊”之名为人所知,她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
许多年后,杨苡依然记得她们三名少女的一次夜行。那是一个除夕之夜,三名少女在沈从文家里守岁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担心她们的安全,但这三名少女却满不在乎地嘻嘻哈哈。而沈从文则笑眯眯地夸赞她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
三个少女就这样踏上了这场夜路冒险,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她们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前进,手中的火把不时晃一晃,以驱散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危险。她们用以壮胆的“武器”,只是每人手中的一根甘蔗。
“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她提议啃甘蔗,三个人便吃了起来,一路只听到她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呸呸”吐着甘蔗渣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亮,让她们一时忘记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依然心怀惊惧的萧珊忽然问道:“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王树藏则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答道:“打!拿甘蔗打!”
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梦
除夕的这次夜行,有惊无险,为联大生活这场美梦中添色增彩。但西南联大的日子,却并非总是这般。1938年9月28日,“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将这样的晴爽的蓝天称为“蓝得像马德里”,尽管没有人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但,就在片刻之后,“马德里”的天空化作了格尔尼卡的惨雾。十分刺耳的声音骤然响起,让人本能地捂住了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
这是一场噩梦,1938年9月28日的这场空袭,只是这场噩梦的开端。炸弹瞬间摧毁了所有罗曼蒂克的传奇。“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逃难的人流中,杨苡第一次见到举世闻名的诗人闻一多,在中西女校时,老师曾带领她们读过他的《死水》,而此刻,这位诗人茫然地站在人流之中,“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
空袭从此成了时刻盘旋在头上的死神。第一次空袭只是日后长期噩梦的预演,对杨苡来说,这并不是对她打击最大的一场空袭。多年后,在写给女儿赵蘅的一段提纲上,她写道:“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此时的杨苡已经嫁为人妻,正在等待预产。
查阅档案便会发现,此时正是日军对昆明空袭的频繁时期。1941年4月8日的空袭尤为惨重,被昆明人称为“四·八血案”,这一天中,日军共投弹82枚,炸毁房屋891间,烧毁房屋1830间。频繁的空袭下,杨苡不得不大着肚子跑警报。恐惧、无助、绝望,或许产妇生理期导致的抑郁症候也加剧了这场噩梦。在这种极其糟糕的情绪下,她给相信足以托付心声的大李先生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发出后,大李先生没有回信,而且从此之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直到晚年,杨苡依然为这封无理的信感到深深地后悔。但直到最后,她依然不知道大李先生没有回信的真正原因。他的弟弟巴金也没有给她一个明确得足以让她信服的答案。
时间就像雪,会掩盖一切,也会融化成水,淡化一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八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刻终结。但狂喜过后,她等来的却是一场悲伤的梦:“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百岁以后,我还好多次梦见过大李先生。有个梦特别奇怪,梦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样的。他喝了酒,发脾气,在前面砸门,老潘子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就嚷嚷:我找她说两句话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门踢开了。进来站在院里对后面喊:我只说一句,说完就走。他跟我说的一句是:我不是赖斯基!我回了一句:这里也没有马克!”
“这梦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从来都是很绅士的,我哪见过他发脾气?梦里成了那样。”
“睡眠不能带给我休息,
我清醒着的眼睛永远看不见,
死去的人的影子,
环绕在我的床前。”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聚与离别。在这生与死萦绕轮转的世间,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一切可能,也都可能被死亡粗暴地打断。许多的岁月之后,历经生死的杨苡回顾往昔,或许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她见证了如此多的生离死别,而别离的场景常常不是一曲挽歌,甚至不是一声呐喊,而是无奈的呻吟,是荒诞的哭嚎。
死亡会夺取一切,但惟一不会夺取的,就是梦。至少在梦中,一切不会那么容易戛然而止,也至少在梦中,生人与死者还可以擦肩而过,握手寒暄,只是分不清梦里的他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自己内心的造相——但唯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梦中浸透的那份情感,无论是思念,追悔,悲伤,还是欢欣,那是等待许久的希望,而希望,本就无所谓真实或虚空,因为支撑这希望穿过一个世纪的岁月,继续等待下去的,是爱。就像杨苡经常引用的那段《哥林多书》中的箴言: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撰文/李夏恩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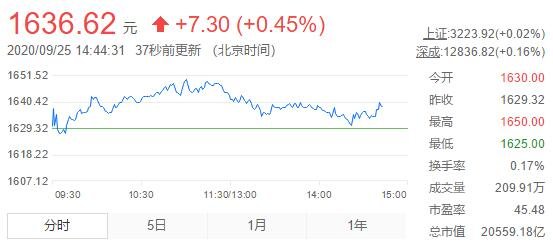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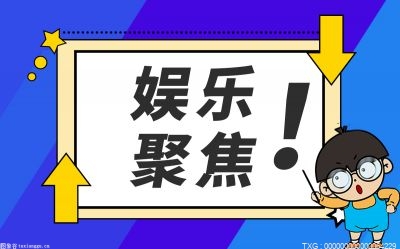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