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胜
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什么,就要首先理解西方现代化“旧道路”是什么,从而在比较中发掘新意。而要理解西方现代化“旧道路”,首先就要理解其所根植的西方文明。美国著名政治学理论家拉塞尔·柯克曾对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的精神源泉,亦即现代西方文明的源流做出了归纳。柯克认为,作为殖民者来源地的欧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无处不在,这些观念渗透进罗马文明,尔后进入中世纪文化,紧接着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进入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思想。
现代西方文明背后隐藏着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
现代西方文明正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两大传统。
首先,西方文明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这种中心主义思想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西方传教士们的“布道精神”。尔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渐趋发展出了一种由信仰中心扩展至经济中心乃至文明中心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心主义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经历了一些辩论,但是由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开启较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从物质基础的角度更加印证了西方社会在现代文明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结论。就西方自身内部而言,在19世纪以前,西方社会一直普遍认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有自己是开化的、文明的,因此,作为“文明”的西语词汇一直都是单数形式,直到19世纪初叶以后,“文明”才首次以复数形式出现,但是西方人对西方文明以外的人类文明的认知却始终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欧美以外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追求自身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过程中都曾一度基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原因,提出了世界的发达文明在西方的文明理论。例如,福泽谕吉就曾这样说:“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虽然也有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提出了反对西方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但是直至今日却始终没能从根本上避除“西方中心主义”论调。这最终表现为,过去的近五百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发展认知中,现代化几乎约等于西方化。
与此同时,西方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传统。在古典时期,希腊的政治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就曾对腓力说过,“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他一生都在为建构一个具有统摄力的“希腊帝国”而奔波,这一信念也多次掀起了“泛希腊化”的政治浪潮。这种“希腊帝国”的精髓就在于对内民主与对外殖民,它是日后欧洲帝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在中世纪,高举基督教教义之传教大旗的十字军经历了数次“东征”,其本质上也是欧洲强国向外进行的殖民掠夺。进入工业文明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了全球的资本扩张和殖民活动,在非洲、澳洲、南北美洲以及亚洲的许多地区,随处可见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的身影。对于殖民地地区资源的大肆掠夺、罪恶的奴隶贸易,甚至是对一些原住居民部落的灭绝,正映衬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西方现代化道路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了来自实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挑战
在“西方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双重逻辑之下,这一最早由西方开启的现代化道路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了来自实践和价值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诉求受到了传统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束缚和限制。这种世界整体的内在发展张力同时就表现为,非西方文明对自身文明性的重拾与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论的反弹和抗争;表现为非西方后发型国家的和平崛起诉求与西方先发型现代化国家“殖民主义”惯习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当前,先发型现代化国家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间在这一道路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开启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无序扩张,“西方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经济垄断、政治霸权和文化意识形态偏见随处可见。这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追求均势发展、不干涉他国内政的政治原则以及对自身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例如曾经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坚定捍卫者和受益者,美国长期在全球范围内奉行长臂管辖战略,同时依靠其发达的技术垄断、金融霸权和军事强权地位,长期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表现得愈发鲜明。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区内部也存在许多既有道路所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例如在欧洲,出现了与其当初构想的民族国家体系渐行渐远的政治新局面,欧洲各国提出了基于主权共享概念的欧盟体系并将其付诸实践,然而却又伴随着英国脱欧公投的通过使其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资本劣根性和政治操纵性轮番上演,出现了一幕幕令世人震惊的“防疫”举措。一方面,在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当中,西方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上的软弱无力、对疫苗的垄断和价格操纵、为达到政党和资本利益而忽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自由主义”原则、为稳定经济指标而实行的无节制通胀的经济政策等,都使得深藏于西式现代化道路的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对那些走在西式现代化道路上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其制度漏洞在重大社会风险面前显得脆弱不堪。例如,印度作为遵循西式现代化道路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典型代表,曾经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捧上所谓“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神坛,却在此次新冠疫情冲击下表现出全面大溃败。这让一切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政治掩饰、吹嘘和借口变得毫无意义,所谓的西方式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荡然无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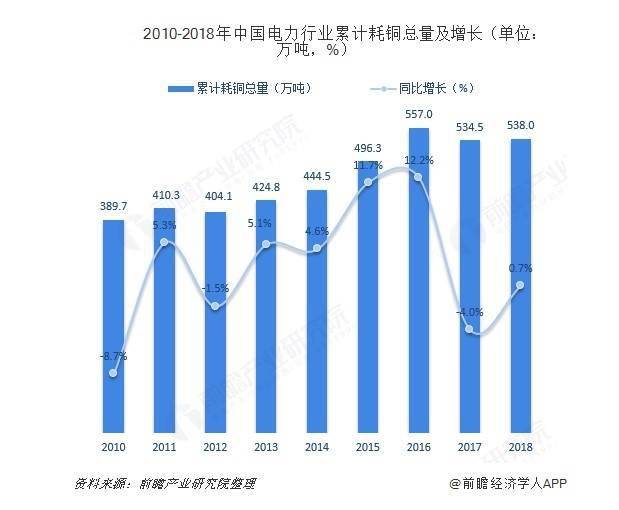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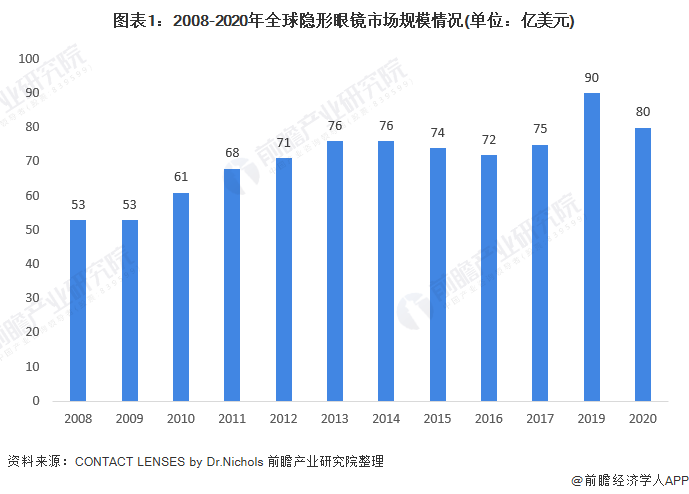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