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时候,对那些脚注或尾注一大片的书,总是会有些抱怨。在正文中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不好吗?干吗非得放到脚注或尾注里?作为读者,一来觉得可能有些有用的知识错过了可惜,但如果看又会干扰对正文阅读的连贯性和完整性;二来脚注的字号都比正文要小,看起来实在费劲。如果是尾注的话,就更增加了读者的负担,在书页之间来回地翻。加入注释是本着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意愿,所以,读这类有较多较长注释的书籍时,就不免要吐槽几句。
不过,吐槽归吐槽,遇到注释篇幅长的书该看还得看,况且在有些书的长篇注释里夹带着不少“干货”,读罢让人收获满满。长篇注释在译作中尤为普遍,有些书每页的正文与注释之间的分割线恨不得靠近页眉,有的注释则更是会恣意地转到下一页,甚至再下页。如果是尾注的话,注释竟能占到一半儿的篇幅,足够再出本书了。比如说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的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正文只是从第4页“导论”开始,到144页就结束了,而它的注释竟从147页排到了252页。然而,细读注释中作者提供的信息,却似乎又是必要且有用的。
注释多的特征,在法学类译著中更为明显,这或许是法学家们更懂得尊重他人著作权的缘故吧。在这些注释中,确实也让读者了解到不少有价值、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法学院——美国法学教育百年史: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就是如此。作者罗伯特·史蒂文斯是一位英国杰出的律师、学者及声誉卓著的教育家。他年轻时在牛津与耶鲁求学,也曾在美国及英国的多所大学执教并担任院长或校长,他尤其对美国法学教育的状况了如指掌,在谈到美国法学院发展的历史时如数家珍,而那些被安排在注释中的信息,也颇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它们与正文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早期美国的律师要想执业,需要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一定时期的学徒式见习。罗伯特认为“学徒见习制,意味着要实现从传统的教学体验骤然转换为接受高强度的压迫甚至‘剥削’”。为说明这一观点,作者用了将近两页篇幅的注释,来说明他为何如此看待学徒见习制。
作者在注释中援引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记录,来说明“最佳状态下的学徒见习制”。亚当斯这样描述自己的导师塞弗勒斯·帕森斯:“对我们来说,律师事务所里有帕森斯存在,算得上最大的福利。他本人就堪比一座法律图书馆,对于法律执业的任何方面都十分精通。但帕森斯最大的优点,在于其乐于解答问题的程度远超弟子们爱问问题的程度。作为一位从来没有被问倒过的导师,帕森斯不仅会就问题本身作答,还会将与之相关的其他关联问题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我开始相信,能有这样一位见习指导老师,算得上是一种福分。”而昆西的父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的指导老师只知道让学徒们大量阅读自然法、普通法、民法及国际法的相关著述,根本没有什么指导。而更多学徒的见习工作,无非是“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文书校对”。
19世纪下半叶,学徒见习制在美国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诟病,因为“就算是最为勤勉负责的导师,也无法为学徒提供一种真正的全方位的训练”。罗伯特在注释中,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当时的见习生们的记录。在律所,见习生们几乎就是靠自学学习法律,因为“对于一位业务繁忙的律师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法律原则指点年轻后辈这回事”。而见习生们在律所中的忙碌也是司空见惯的,在费城,约翰·马歇尔·盖斯特这样记录他的见习生活:“见习第一天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无论是研读沙斯伍德对于布莱克斯通法学观点的阐述,还是从格式条款中总结各种令状或戒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这就是我每天见习的常态。我们这些见习生们,需要负责向法庭书记官提交法律文件,起草法律协议,参与质押、抵押等类似合同文本的制定,出席公开拍卖。我们需要作为产权保险公司代表,前往合同登记办公室、遗嘱注册办公室等地进行不动产流转与抵押调查……我们,就是以这种方法,把法律学到了手。”
从这些注释中,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美国学徒见习制的样态,正是基于此,美国的法律教育才从学徒制逐渐转变为学院制。而这些资料则需作者在大量的日记、笔记中进行细致的爬梳和整理,其背后所记录的是学者严谨枯燥的学术生活。从这一点来看,学术著作中的注释同样有阅读的必要,这也是对作者劳动的一种尊重。不过作为读者,倒是想提个建议,出版社若能把注释也改用正文的字号则会更好,这或许不符合编辑惯例,但却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何乐而不为呢!马建红(法学博士) 漫画/陈彬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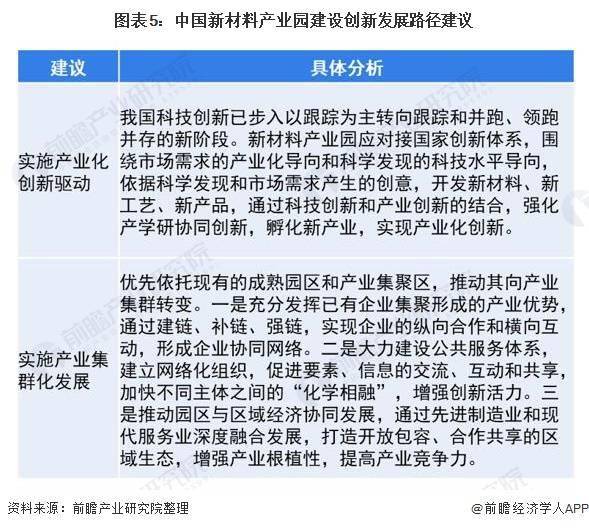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