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武汉市蔡甸区李集村,一名老人撬出一株带根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向记者示意,黄花根状茎末端已经长出新的枝芽。 新京报记者 吴梦真 摄
短短半个月时间,“加拿大一枝黄花”就从一个直白得近似不正经的陌生植物名,迅速成为让武汉市民“见花即上报”的切身威胁。
在一次次科普中,它被勾勒出清晰的影像:原产于北美洲,桔梗目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高可达2.5米,花期顶端绽开一簇簇颜色鲜亮的小黄花。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被引入我国,曾被用作插花中的配花。后逸生为恶性杂草,肆意与其他植物抢夺水分、营养和生长空间,“一花开后百花杀”。2010年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二批)。
今年10月,武汉市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被这种花疯狂攻占,农田、果园、林地、护坡、高速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其身影,绵连两三公里成片生长。为此,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等8部门联合召开“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工作会议,控制扩散蔓延和危害影响。
在武汉乃至湖北之外,与“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战事”,也相继在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十余个省份打响。
入侵
从“黄莺”到“恶魔之花”
G0422武深高速公路笔直地从江夏区西面穿过。驾车行驶其上,一团团盛开着黄花的高大植株不时撞进眼帘。有的是一株两株,有的大片蔓延出100多米,在高速路的一些三角地带,它们更是肆意生长,模糊了立冬之后该有的萧瑟。
驾驶位上的褚世海却有些忧心忡忡,“怎么会这么多……”他是湖北省农科院植保土肥所杂草与外来入侵生物研究室副主任,准备带新京报记者去探访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一处茶园。2007年,他第一次在那附近的山脚下见到“加拿大一枝黄花”,“当时只是两三株,现在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而实际的踩点结果并不乐观。原来仅有两三株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已经长成了一小片,遍布这个一米多高、三四十米长的小山坡。
褚世海介绍,“加拿大一枝黄花”主要通过地下根状茎和种子两种途径进行传播:在生长过程中,地下根状茎会不断向周围蔓延,形成新的植株,第一年也许只有零星几棵,但第二年、第三年可能就会爆发;种子的传播能力则更为强大,每株可以生产20000颗种子,它们带着冠毛,能像蒲公英一样,借助风力作用,动物、人类活动或交通工具等方式传播到更远的地区,造成灾情扩大。
“这就是‘黄花过处,寸草不生’。”拨开手指粗细的植株茎秆,只见光秃秃的土层之上,已全然没有其他植物的踪迹。褚世海解释道,“‘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生存竞争能力很强,扩散之后,会与其他植物抢夺水分、营养和生长空间,造成本土植物不断凋亡。”
这样的场景已经在蔡甸区一处玫瑰园上演。鹊巢鸠占后,种植的玫瑰被“加拿大一枝黄花”挤兑得无法生长,商户不得已只能将玫瑰园整个翻耕,曾经漂亮的园区如今已是光秃秃一片。
“一花开后百花杀”。这种原产于北美洲的菊科植物,因花色亮丽,1935年,作为观赏植物被引入上海、南京等地,常用于插花中的配花,鲜切花市场称之为“黄莺”。后逸生为杂草。有资料表明,它的入侵,已造成上海30多种本土物种消失。
曾经的“黄莺”成了生态杀手、“恶魔之花”,被列入了《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二批)。褚世海说,目前,国内没有“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天敌,如果任由其生长扩张,再过一两年,消灭它的难度会成倍增加,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清除。
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刘胜祥教授,是那个拉响“入侵警报”的人之一。10月22日,他在武汉市江夏区进行野大豆资源调查时,发现了一片长约2公里的“加拿大一枝黄花”群落,“沿着一条正在建设的高架桥边的水沟,呈现疯长态势。”
这引起了刘胜祥的警觉。研究植物资源与生态评价近四十余年,他深知任由这种恶性杂草蔓延会造成何种影响。此后他便时刻留意这种恶性杂草的分布情况。“11月1日,我们到十堰市。我发现,原来一直没有‘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十堰市,竟然也出现了这种植物。”
刘胜祥心急如焚。他介绍,目前“加拿大一枝黄花”的主要防治方法,一是机械清除并焚烧,二是在其花蕾期施用化学药剂使其不能正常结实。“加拿大一枝黄花”10月中下旬开花,11月底至12月中旬果实成熟,当时已经到了盛花期,错过了化学防治时机,但种子还未成熟,一个最简单的应急处置就是把正在开花的花枝折断,以便抑制其次年的入侵面积扩大。
经过进一步调查,11月4日,刘胜祥撰写文章并上报给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湖北省城市留言板上已经有一部分留言,再加上刘胜祥教授的反馈,很快省里就下了批示,要抓起防治工作。
11月10日,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等8部门联合召开了防除工作会议,要求在11月20日前完成包括农田、道路、风景区等全市地面上的防除任务,并号召武汉市民若发现“加拿大一枝黄花”,拨打农业农村局的热线电话举报。
就此,武汉开始了一场对“恶魔之花”的围剿。
防除
一个街道仅一个村没有发生“黄花”灾情
入侵从高速公路一路延伸到村庄。“加拿大一枝黄花”悄悄在村落田地间扎下地盘,甚至堂而皇之地占领了“无主之地”。
武汉市中心向西约50公里是蔡甸区索河镇李集村,11月中旬的田地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一片枯黄的底色中,那些叶片油亮、开满黄花的植物,抢眼得有几分突兀。
防除工作开展后,为系统梳理发生面积、已清除面积,当地成立工作群,每个村都会按土地用途分类统计相关数据。根据该工作群里的粗略统计信息,截至11月16日,索河街道下辖的20多个行政村中,仅有一个没有发生“加拿大一枝黄花”灾情。
“往那边的田里走走,很明显,一眼就能找到‘黄花’。”在李集村,许多人更习惯将那个冗长的称谓简称为“黄花”,以前没有见过,今年突然长满了田边地头。“9月份的时候开花,那块地里一连片都是,黄灿灿的,看着很漂亮。”漂亮,是“加拿大一枝黄花”留给王女士和其他村民最深的印象。没有人深究它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村民们口中的“那块地”,就位于老卢的家门前。老卢说,这块地已经有三四年没人耕种,此前已满是杂草,轻易没人进去。如今,不请自来的“黄花”扎根了,但是听说“黄花有毒”,老卢很少主动去碰,只是前几天家门口的花池里冒出了两株,怕影响自己种的花,他才动手将它们拔除。
另一片荒地里,两位老人开辟了一片菜园,70多岁的李老太太正在给菜浇水。几周前,因为担心高大的植株挡住阳光影响蔬菜生长,他们用镰刀将菜园周围的“黄花”砍掉了一大片。老人还用力撬出一株带根的“黄花”向记者示意,只见密密麻麻的根须里,一条根状茎上甚至已经长出新芽。
其实,早在10月底,李集村已经进行过一次统一的大清理。那一次,村里请来的五六位村民干了整整10天才清除掉,每名工人一天100块的工资。但这仍难以阻挡“黄花”小片零星地发生,村委会只能多进行动员,希望村民能主动拔除。
那些天,类似的场景也在武汉其他区域上演。11月19日下午三点多,在江夏区金口街道南环公路附近,一位30多岁的男人,正带着六名女工拿着镰刀埋头除花。男人是附近村庄的负责人,也面临和李集村同样的瓶颈——清除专项资金还没到,自己只能出低工资请女工清理。
一位女工说,清理中时不时会遇到带刺的野草和小灌木,会将人划伤。另外,一旦开始割除,草丛灰土飞扬,也很呛人。“有的花枝干能长成小树苗一样粗细,很难拔出来。”
战线
武汉拉起群防群控网
“有没有谁知道,最近这波清除运动是怎么发起的?为什么要干这种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11月18日,武汉市治理工作专班负责人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条来自大学同学的疑问,“他很纳闷这个事。我就给他留了个言说,我知道这个事,可能和我有关。”
该负责人表示,去年武汉疫情,为解决信息不通畅造成的水产品供应链断裂问题,他也曾在网上公布需求信息,同时也公开了部门电话、供应商电话,“利用群众的力量解决群众的问题”,效果非常好。
有了这次经验,面对“加拿大一枝黄花”,他自然萌生出一个想法,“武汉市有8000多平方公里,整个农业系统加起来才多少人?所以我就想到要发动群众。”在这位负责人看来,防除工作是一项常规工作,“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爆款话题。”随着#武汉市民看到这种花请上报#的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的热线一天能接到几百个来电。
新洲区宋寨村的张先生就是积极响应者之一。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消息后,他所在的街道也开始动员村民寻花。“10月底,我在自己的桃园里也发现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身影,就查了一下资料,还拍了抖音视频,没想到很快就成了热门。”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局联合武汉市多个部门,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农业农村局负责农田撂荒地;园林和林业局负责绿地、林区、自然保护区;交通局负责国道、省道铁路沿线;水务局负责河、湖、库区、岸边;文化旅游局负责风景名胜区及景点的治理……
“必须是群防群控才能做好这个事。”前述武汉市治理工作专班负责人介绍,截至11月20日,武汉市已开展集中行动52次,各区筹措除治资金576万元,参与人数24756人次,动用机械438台次,完成防治面积83%,治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如今回头看,这位负责人欣慰地说:“之前省里有一项任务,要求在2025年之前,摸清外来物种的分布情况,现在通过这件事,基本帮我们实现了(任务目标)。”
热搜出现后一度很紧张的治理工作专班团队,看到媒体的评价后,感到自己的做法得到了认可。不过,他们依然不敢放松警惕。该负责人介绍,因为超强的繁殖能力,“加拿大一枝黄花”防除工作不是一年就能彻底完成的。现在,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已经着手在做点位图,“上面标注出今年分布的点位、经纬度,包括了发生的面积、危害程度。这样明年再进行清除,就能省去很多人力物力。”
农业农村局请来研究外来入侵植物方面的专家一起商讨,“我们会让专家给每个区的人做培训,每个区再向下做培训讲授防治方法。可以培养成很多个防治专家。”治理工作专班负责人说。
前段时间,索河镇农业办召集各村干部,统一做了防除工作培训,如今谈起防除方法,李集村村干部李凤侠已经十分老到:“第一,我们请人把花的枝叶割掉并集中焚烧,防止通过种子传播;第二,要对其根部进行彻底铲除,发生面积大的地方统一用挖掘机挖,发生面积小的地方用人工铲除;第三,虽然今年已经清理一部分,但等到明年三四月份还要再用农药、除草剂对这些地方进行二次清除。”
李凤侠说,这些防除的方法“都是上面专家讨论出来的”。而李集村之前被“加拿大一枝黄花”填满的荒地,经过再次翻土后,已经种上了菠菜。
探索
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生态防治
自武汉报告入侵后,“加拿大一枝黄花”也相继在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十几个省份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植物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相伴而来的,也有不解和争议。有人认为,不应该将其一棒子打死,可以针对花的价值进行利用,网友也纷纷评论:“‘加拿大一枝黄花’有药用价值”“可以学习国外炼精油”“可以推广到其他植物难以生存的土地上”……
对此,褚世海表示,“加拿大一枝黄花”确实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它提炼出的精油也可以做化妆品,枝干可以造纸,幼苗可以喂马牛羊,“但这些并非不可替代。”褚世海强调,鉴于该花对生态平衡、生物多样性以及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作用,防治起来又非常困难,其带来的危害已经远大于可利用价值。
也有人担心,“全民清理”可能因为难以辨别而“一刀切”,威胁到本土一枝黄花的生存。
对于这一点,褚世海认为不必过分担心。据他介绍,本土一枝黄花属于一般性杂草,分布范围不广泛,密度也并不大,在武汉,甚至很少能见到本土一枝黄花。刘胜祥教授也表示,“加拿大一枝黄花”经常长在路边开阔地、阳光充足处,而本土一枝黄花主要在无人的山区生长,且多在林下、草地,很难形成群落,“很少会有误伤。”
在武汉市应急管理专家、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卢新民看来,防治工作有热度、有讨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次吸引了很多人关注,也会让更多人来了解入侵的外来动植物,可以促进全民科普。”
在卢新民看来,治理外来入侵物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他以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2003年即被列入的《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第一批)的喜旱莲子草(俗称水花生)为例解释道,目前莲子草已经成为农田常见的一种恶性杂草,由于该草具水陆两栖特性,还会威胁水利渔业、本土生物多样性,“但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防控技术。”
卢新民提倡在其他防控(如化学、物理或生物防控)基础上,对外来入侵植物进行生态防治。所谓的生态防治,就是通过筛选、构建本土植物群落,逐步替代入侵植物;恢复本土生态系统功能、提升本土植被“免疫”新物种入侵等能力,最终实现对入侵植物的可持续防控。
前几天,他的学生也到武汉市蔡甸区做了“加拿大一枝黄花”的相关调查。“这种入侵植物肆意生长,可能与本土生物多样性降低、耕地抛荒有关——如果构建一个稳定的本土生物群落,它(的生长)是不是可以被抑制?”为此,卢新民正在做着大量的调查和实验。
中国是遭受外来物种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威胁或具有潜在威胁并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219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今年4月15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物安全法》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法律基础——防范物种入侵,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相关部门守土有责,对于蔓延和爆发的外来入侵生物,及时采取果断举措。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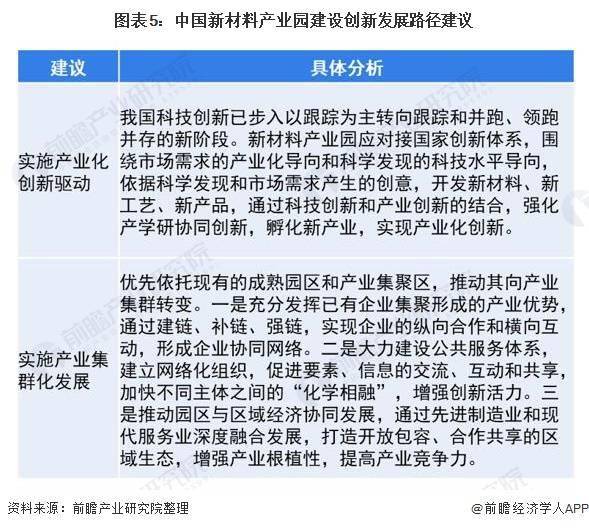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