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超过425万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的病例超过35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0万,是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不仅此刻不反思为何抗疫不力,反而处心积虑地把病毒溯源政治化,拼命抹黑中国,试图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事实上,近期关于美军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基地和新冠病毒起源的诸多疑点,已经越来越指向美国军方情报机构和一些美国政客,德堡黑幕的背后“鹰的阴影”越发清晰起来。
拉尔夫·巴里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流行病学家,因长期研究冠状病毒,而被美国媒体称为“冠状病毒之父”。
2020年11月,巴里克在接受意大利媒体“普蕾萨迪雷塔”采访时,提到了实验室合成病毒的可能性。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教授 拉尔夫·巴里克(2020年11月):我们在实验室改造任何东西,我们称之为“签名突变”,就像是你要进行一个突变,就在(基因片段上)写下该物质来自巴里克实验室。
记者:但如果你不想留下签名,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是吗?
巴里克:没错,你可以不留签名进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法,利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
而在意大利记者带有政治目的的诱导下,巴里克开始胡编乱造,迎合西方记者的思路,把不实言论指向中国。
巴里克:如果你想问病毒是否在之前就存在,那只能去看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记录。
而事实上,在实验室进行“病毒改造”,巴里克本人才是世界公认的“顶级高手”。
2002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系统,这样可以在活体内改变病毒的基因或结构。
2008年,巴里克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团队如何完成“人工制造冠状病毒”的“独门秘籍”。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命形态。”
“这项研究完成了一种全长29.7kb的SARS样冠状病毒的从头设计、合成和激活。”
在这篇论文里,巴里克宣称,自己发明的“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气道上皮细胞。巴里克强调,只需要使用商业合成的DNA“碎片”,就能造出一个病毒。
2020年6月12日,巴里克做客美国“本周病毒学”博客,进一步阐述他的自己的团队在自己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的细节。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教授 拉尔夫·巴里克(2020年6月):关于建立新冠病毒的老鼠模型,问题是新冠病毒不能在老鼠体内生长,也不能与老鼠的ACE2受体结合,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将至少四或五组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的受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老鼠的ACE2受体结合。(谈到两处对新冠病毒受体结合域的修改时,)其中一个是我们所知特定的(氨基酸)残基,这个残基与人和老鼠的ACE2受体的相互作用是不同的,另一个残基是邻近的脯氨酸,我就是不喜欢脯氨酸在那附近,所以我们就改了。因为我们能做到所以就做了,所以一般来说如果那里有个脯氨酸我就是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我为何不喜欢脯氨酸,但我就得把它拿掉。
巴里克这番对“病毒改造”的生动描述,立即遭到同时在线的另一位嘉宾的调侃。
播客嘉宾(2020年6月):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利用“功能增益”的思维过程。
直播间气氛顿时陷入尴尬。
“功能增益”一直是个敏感词。“功能增益”是指通过改造生物体的致病性、传染性或宿主范围,帮它发展出新的“能力”或“功能”,通俗地说就是加强病毒的毒性。
由于这项研究存在风险。2014年发生的一系列安全事故促使美国政府叫停了“功能增益”研究,但该禁令于2017年被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实验室本身带有“功能增益”性质的研究却一直在进行,而且该实验室的安全记录并不良好。
据北卡罗来纳大学2012年到2018年这6年的年报来看,该校的生物实验室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大量的事故,而且除2016年外,都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12年的年报显示,当年该校的生物实验室有8起涉及实验室泄漏的事故被调查,涉及的是潜在具有传染性的物质。在2013年的年报中,这个事故数字增加到了12起。2014年被调查的生物实验室的事故数量继续增加到13起。2015年,实验室发生事故14起。尽管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8起,可在2017年时这一数据竟一下子爆增至42起。2018年则进一步增加到了43起。
据美国新闻网站ProPublica公开的资料显示,自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1日,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报告了28起涉及冠状病毒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6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
“UNC研究人员报告6起实验室制造冠状病毒事故”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个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实验室中,在进行涉及转基因冠状病毒实验时,发生了老鼠咬伤、病毒溢出以及其他事故。”事故发生后,北卡罗来纳大学拒绝公开有关事件的关键细节。尽管备受争议,巴里克却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2018年,在一场关于预防流感的会议上,巴里克在演讲中大谈如何赚钱。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教授 拉尔夫·巴里克(2018年):我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任何情况下总有赢家,如果你准备在下一次大流行中大赚一笔,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那就购买防护服制造商,或为流行病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公司的股票,你或许能赚不少钱。
而2018年以来,巴里克就与美国吉利德药厂合作,开展了寻找能应对SARS和MERS病毒等冠状病毒的药物的工作。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系教授 拉尔夫·巴里克(2018年6月):吉利德在对抗艾滋病病毒和丙肝病毒的药物研发方面享有盛名,我认为他们也意识到了,进入这一领域(冠状病毒药物研究),针对一种新出现的,且可能具有相当大危害的高致病性病毒,进行药物研发可以带来的机会。
7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意大利国家肿瘤研究的科学家们在一篇新论文中写道,两家实验室对疫情暴发前采集的少量血液样本进行的重新检测表明,存在通常会在新冠病毒感染后才能观察到的抗体。
2020年11月15日,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与意大利锡耶纳大学的学者在《肿瘤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新冠病毒可能最早于2019年9月就出现在了意大利北部地区,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调取了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间自愿参加肺癌早期筛查的959名体检者的血液样本。他们发现,在11%的样本中发现了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其中既有2019年9月采集的样本,也有2020年2月采集的样本。超过半数的新冠病毒抗体阳性样本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
今年7月7日,意大利媒体《声音的力量》发表的一篇名为《源于德特里克堡 美军血液项目把病毒带到了意大利》的文章指出,美军借助“武装部队血液项目”的传播路径,不应被忽视。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又被称为“星条旗血液项目”,是美军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美国海外军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美国“武装部队血液项目”主任 杰森·科里:对国防部来说,我们的任务是给海外的战士和医务工作者提供血产品。
它从美国国家中心地区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其中就包括德特里克堡。然后每两周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意大利的空军基地,要求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
据报道,2019年8月,位于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
而不容忽视的一个细节是,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销毁“医疗废物”的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名为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的私人公司处理。
然而,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十几万美元。
环境质量部门在该公司地面积水中检测出大量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员工不穿任何防护服等现象。
巧合的是,也是在2019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对德堡进行检查,指出该基地出现许多异常情况和令人不安的数据。尤其提到一起未指明的与“生物防范”有关的“事故”。
随后,德堡因“涉及国家安全”被关闭。
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而从美国“抗疫不利”的回顾,也很容易品味出最初隔岸观火的美国政客,如今拼命“甩锅中国”的真实动机。
就在德堡黑幕掩盖真相的同时,有一个人,则站出来揭露出德堡上空的“美国之鹰”是如何导致疫情失控的。里克·布莱特,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前局长。
按照应急预案,卫生部防备和应对助理部长罗伯特·卡德莱茨是总协调人。卡德莱茨不仅是职业空军军官,还是一名生化武器专家。
布莱特:2020年1月18日,我问了卡德莱茨,是否我们应该召开一次灾难领导人会议,令我震惊的是他的回答是我看不出有什么紧迫感。
而据2020年3月19日《纽约时报》披露,2019年8月,美国卫生部和疾控中心曾举行了名为“赤色传染”的大型传染病防护演习。
“赤色传染”模拟的是2019年6月19日,假设暴发的一场“呼吸系统疾病”大流行。而这一设想的最初来源是2018年11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牵头的一次会议。
但令人不解是,既然是纯假设性的事件,为什么病毒暴发地点偏偏设定为中国的“西藏”?“赤色传染”这一名称也很容易使人产生“黄祸”和“冷战”的联想。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就在1月18日当天,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向正在海湖庄园高尔夫球场打球的特朗普汇报新冠病毒情况。但特朗普却打断阿扎尔,抱怨起阿扎尔推行的禁售电子烟政策。
而此时的美国,正遭受神秘的“电子烟肺炎”的困扰。截至2020年2月18日,电子烟肺炎感染人数为2807人,死亡68人。但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电子烟肺炎却神奇地消失了。
2020年1月21日,当特朗普抵达瑞士达沃斯时,美国已经出现第一例病例。
记者:CDC发现第一例确诊为新冠肺炎的病例地点在华盛顿州,你听说过CDC的简报吗,现在还有人担心流行吗?
特朗普:我有。完全不担心,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只有一个人从中国来,一切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一切都会好起来。
美国公共广播网把美国暴发的疫情描述为一场“华盛顿州”与首都华盛顿的“双城记”。
2月23日,特朗普照常访问印度。
医疗记者 卡洛琳·陈:整个体育场人满为患,超过10万人,这次集会开始了,一次旋风般的旅行,充满了总统所热爱的华丽场面。
2020年2月5日,CDC开始发放有缺陷的新冠检测盒,这被福奇看作是一项决定性的失误。
记者:CDC设计的测试有三个组成部分他们称为N1N2N3分析,N1和N2检测专门寻找新冠病毒,但是N3检测却多此一举,检测冠状病毒,我不知道为啥他们非要把第三部分也加进去,因为检测根本就不需要,但是第三部分却是导致所有问题的原因,第三部分纯粹是个污染物。
与此同时,美国却奇怪地拒绝使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新冠检测盒。同时,美国药监局无理由停止新的检测方法的审批。
于是,使用被污染的官方试剂盒检测不出病毒,使用别的方法检测出了病毒,官方不承认。美国本土患者得不到检测,自然就没有人“感染新冠”,于是,疫情就得到了“控制”。
特朗普:我喜欢美国确诊数字停在这里,我不需要数字翻番。
而此时,一些医学人士已经开始把电子烟肺炎症状与新冠肺炎的症状进行比较,并提出怀疑。
前卫生部长 凯瑟琳·西贝柳斯: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政府是在故意拖延检测。
3月11日,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承认,一些误诊患者,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美国众议员 哈利·荣达:所以有些美国人看起来似乎死于流感,其实可能死于新冠肺炎。
雷德菲尔德:迄今在美国实际上已经以这种方式检测出了一些病例。
福奇:这是一个失败,让我们承认吧。
布莱特在《华盛顿邮报》写道,“政府对真相的敌对态度以及把疫情应对政治化的做法危害了公共卫生与安全,导致成千上万人本可避免的死亡……”
7月20日,美国抗疫队长福奇和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保罗不仅试图栽赃中国,也把锅扣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机构、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的头上。
此前的5月19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声明,从未批准任何支持对新冠病毒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拨款。此次旧事重提,引起了福奇的愤怒。
福奇:这都成了模式了,每次听证会反复纠缠。他谈到“功能增益”已经被合格的专业人士反复评估,不符合“功能增益”的定义,我在国会没有说过谎,当然也从没有在国会说过谎,可以结案了。
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秘密研究和神秘关闭,以及2019年美军是否在参加武汉军运会时传播了病毒,更是疑点重重。
一年前的2020年6月30日,著名五角大楼记者汤姆·斯奎蒂耶里曾在《美国瞭望》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军运会会传播新冠病毒吗?》
作者在文章在提到,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代表团,包括188名运动员、24名教练员、18名队长、14名医疗人员、10名裁判、9名官员、7名高管、9名军体委员和2名国务院人员。
当为期9天的比赛结束后,美国运动员返回了25个州的至少219个基地,但返回后,直到2月1日,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新冠检测。
一位五角大楼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解释说,这是因为武汉军运会是在新冠暴发前举行的。
但美军方在2020年3月31日统计时发现,至少有63个已经发生过疫情的美军设施,派出过赴武汉军运会的运动员。而这些美军当时都是通过西雅图的塔科马国际机场的包机来回的。而华盛顿州正是美国早期疫情暴发地。
令人遗憾的是,美军一直未披露参加过军运会运动员的具体情况。记者斯奎蒂耶里注意到,美国国防部对这个话题“三缄其口”,甚至关闭了有这个话题的记录,理由是“安全原因”。
而2020年4月14日,当国防部长埃斯珀在记者会上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声音在网上发布后也“神秘”地消失了。
当时在现场的斯奎蒂耶里目睹了这一场景。
记者:为什么在武汉参加运动会的运动员和支持团队没有被检测?
埃斯珀(埃斯珀回答了但声音消失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就连在溯源问题上极力反华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也引用了中国官方对美军可能在武汉军运会上传播病毒的质疑。
美国众议员 迈克·加拉格尔:我们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即解密所有的情报,马上,拜登政府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让信息完全透明。
加拉格尔为此要求美国军方提供数据以证明清白,但未能得到回应。那么既然美国议员也提出调查要求,美国军方为什么还刻意回避对美军德堡的溯源调查呢?
以政治化病毒溯源为抓手,妄图误导国际社会,甩锅污蔑他国,这样的做法让人不禁回想起1918年那场夺去无数人生命的大流感。
在大约18个月的疫情期间,全球病亡人数大约是五千万到一亿,比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还要多。
然而,这场被称作“西班牙流感”的恐怖疫情其实并不发源自西班牙,那么究竟是谁让西班牙背了一个多世纪的黑锅呢?
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家 巴里: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疫情其实发源于堪萨斯。
根据美国历史频道考证,最早的疫情暴发地是美国堪萨斯州的莱利堡军事基地。
1918年3月4日,一名叫阿尔伯特·吉切尔的陆军二等兵向莱利堡的医院报告自己出现了头痛、嗓子痛、发烧等感冒的症状。
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家 巴里:第一个被报告的病例,是在1918年3月初,他是个厨师。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教授 卡波佐拉:他的工作主要是处理食物,每天都会有成百上千的士兵,吃到他烹饪的食物。
很快,吉切尔的100多名战友都报告了类似的症状。五个星期内,莱利堡基地有超过1100人感染了这种可怕的流感,最终导致46人死亡。然而,美军并未对莱利堡基地实施隔离,美国政府还有更重要的关注点。
当时,美国已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希望尽快把更多的美国大兵部署到欧洲前线。
就这样,美国军队将这种新型流感带到了欧洲,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几乎蔓延到了每一个欧洲国家。而在美国国内,唯恐影响士气民心,媒体选择性漠视了这场灾难。
美国历史学家 汉密尔顿:交战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都有新闻审查制度,不想让大流感的消息影响战争。
而西班牙在一战中是中立国,没有新闻管控,西班牙认真统计了感染和死亡人数,连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被感染的消息都公开见报。
于是,为了隐瞒本国疫情,美国开动宣传机器,歪曲事实刻意“甩锅”西班牙,渲染“警惕来自西班牙的流感”,让很多人进一步加深了误解。
在当时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频繁出现“西班牙流感”的称呼。
西方流行的防疫海报中,流感的形象是一位头戴面纱、身着长裙,拿着弗拉明戈折扇的女性。
在这张拍摄于1918年费城海军飞机制造厂的告示中,第一行也大大地写着“西班牙流感”字样。
据美国科尔比学院历史系教授拉斐尔·舍克称,在流感大暴发的最初几周,美国社会中还流传着“德国潜艇向美国释放病原体”“德国制药企业故意在阿司匹林中注入病原体”等阴谋论调。
不难看出,为了掩盖疫情真相,美国强烈希望把流感大流行归咎于其他国家。美国历史频道指出,正是这番否认与掩盖事实真相的操作,助长了病毒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1918年的大流感带走了超过50万美国人的生命,冲击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失业率一度飙升至11.7%,暴力和动乱席卷了全国,这也为十年后的经济大萧条埋下了伏笔。
尼日利亚资深外交官 塞里基:新冠疫情给美国带来了经济下滑,影响了就业以及家庭和个人收入,美国政府需要一个借口来告诉民众,遇到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他们打出中国牌试图来解决国内某些矛盾,并不一定是真正关心疫情和病毒起源。
“后坐力”是美国中情局的一个专业词汇,意思是,美国过去执行的某些政策,会在多年后,对未来产生某些“不可预见”的影响。而这些“后坐力”与当年以“先发制人”名义开的那一枪的力学效果,其实是相同的。
这可以通过各种事例来证明。比如美国用搜集来的所谓“洗衣粉罪证”发动伊拉克战争,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导致美国本身的大乱局。
而在“疫情溯源”这些本来应属于严肃科学领域的问题上,美国政客撒下弥天大谎,拼命栽赃陷害中国,反而暴露出美国军方和政客,在疫情暴发前和应对中存在的诸多疑点。
而这种种疑点已经不能简单用CIA所说的“后坐力”来形容。那么,人们不禁要继续追问,德堡军事基地和海外基地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秘密?美国政客在疫情溯源问题上处心积虑搞政治操弄,究竟想掩盖什么?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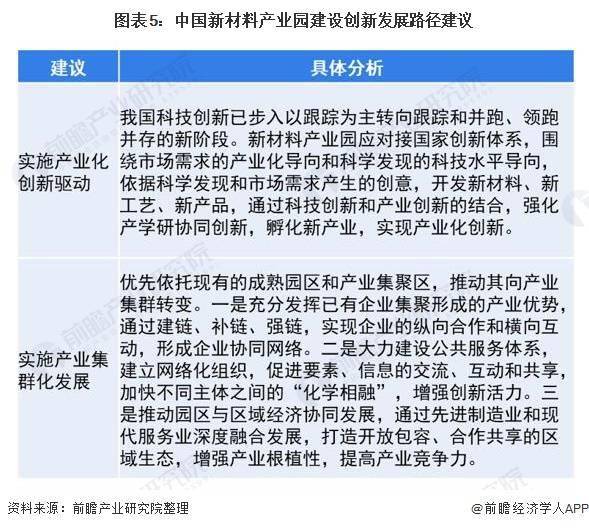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