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智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展览: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
展期:2023.3.16-6.15
地点: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迎来了“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犍陀罗艺术展,共展出203件(套)文物,其中173件(套)来自巴基斯坦各大博物馆,多为考古发掘所得,余者为故宫博物院旧藏。这些文物共同构建了犍陀罗美术辉煌与没落的历程,其中故宫藏品再现了犍陀罗美术的余晖。
“譬若香山”出自佛经。据记载,释迦牟尼出生在迦毗罗卫国都城,都城附近有一座著名的山:犍陀摩罗,翻译过来就是香山、香水山、香醉山等。释迦牟尼在世时,他的弟子许多都在香山修行,之后也有很多信徒在此修道。
犍陀罗美术辉煌成就的取得,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背景密切关联。犍陀罗位处亚欧大陆心脏位置,其范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此地生活着包括波斯人种、希腊人种、中亚细亚人种在内的多民族,尤其是希腊人种及其文化的涌入,显著改变了这里的文明生态。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标志着希腊化时期的开始,而犍陀罗作为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和殖民之地,在其后的数百年间盛行希腊化文明,留下大量相关遗存。不过,在犍陀罗发展起来的希腊化文明,是一种重新被融合和改造过的文明。众所周知的犍陀罗佛教美术,就是以古希腊雕刻技术为基础来表现佛教题材的艺术形式,二者的融合形成了新的艺术传统。
希腊化的早期佛教艺术
展厅入口处有一件名为《河神像》的古希腊风格雕塑。河神斜倚在台座上,头部有浓密的头发,高鼻梁深眼窝,络腮胡子,右手拿着丰饶角,身体极为壮实。神像的五官结构是古希腊雕塑中常见的特征,而丰饶角则是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在西方古典雕塑中较为常见。不过,雕像的身体造型却与古希腊的雕塑传统并不一致,后者神像的制作遵循一种和谐的人体比例关系并以完美的肌肉形态为标准;而这尊斜倚的神像不见严谨的骨骼、肌肉结构,腹部也没有迷人的六块肌肉,其注重肌肤质感的审美趣味,与古印度夜叉雕刻传统相近。可见,这件希腊化文明背景下制作出来的神像,完全以一种文明融合的态势出现。
《二妇争子本生》是一件较早将古希腊雕刻技术和佛教题材结合起来的作品。所谓本生故事,是指佛陀前世累世修行时所经历过的种种善行,常见于各类佛教经典和美术作品中,其中《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等故事绘制于敦煌莫高窟并广为人知。二妇争子的故事在《本生经·大隧道本生谭》有载,讲述的是母夜叉抢了别人的小孩,强辩说是自己的儿子,与孩子的母亲争吵起来,后求助于菩萨明断此事。菩萨在地上画一条线,将孩子置于线上,命二妇拉拽孩子,胜者便抱走孩子。孩子在拉拽过程中大哭,生母心疼,便松开了手。于是菩萨认为心疼孩子者必为其母。而这位聪慧的菩萨就是释迦佛的某一前世。二妇争子的故事流传很广,在中国古代就有多个相似的故事记载。这件雕刻工致的作品中,二妇留着希腊式的波浪长发,面型和身材皆圆润丰腴,身上衣装褶皱的结构与古希腊女神像高度相似,但其厚实的质感又与希腊女神身上的轻薄衣装区别明显。值得注意的是,犍陀罗美术中佛陀袈裟都雕刻成这种厚实的质感,成为类型化的存在。
现代学者认为,早期的佛教并没有礼佛拜像的说法。释迦佛圆寂后,佛弟子和僧徒们坚持不懈地修行,以期从生死轮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所以无须礼拜具体对象。然而,在家的信徒需要礼拜某种能作为精神和灵魂支柱的对象,于是去释迦佛的诞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槃地拜谒,以此来怀念释迦,并起塔供养释迦的舍利。这就是最早的佛塔窣堵波。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圣物崇拜的美术形式。所谓圣物,是指释迦佛的舍利(遗骨)、供养舍利的窣堵波(佛塔),以及释迦使用过的东西,比如衣、钵等,还包括与释迦有关系的圣树(菩提树)。
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发展,佛教教义与信众最终达成和解,逐渐开始制作偶像形态的佛像,此时距离释迦佛圆寂大约有五百年了。展厅中展出的《礼拜悉达多的头巾》,表现了诸神前来朝拜悉达多(释迦太子)头巾的场景。在犍陀罗美术作品中,并未表现剃发的场景,因此悉达多的头巾是一件颇为罕见的圣物。头巾被置于宝座上,宝座有华盖、帷幔,宝座后面的供养者手持拂尘,精心打理供养的圣物,整个画面庄重并充满神圣气息。
佛陀的传记
佛传故事,是表现佛陀化现世间的人生经历,包括释迦佛自诞生到涅槃的各种行迹,其中还加进了一些当时印度大众的意识和想象,以及汲取了当时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在犍陀罗美术中,有将释迦佛的生涯以编年的方式雕刻在窣堵波周围的传统。这些佛传故事遗存数量众多,其中,“燃灯佛授记”尤为重要——这既是释迦本生故事的结束,也是佛传故事的开始。
燃灯佛也译为普光佛、锭光佛等,是一位闪着光辉的过去佛。“燃灯佛授记”不见于中印度,但在中亚却备受欢迎。故事讲述的是在很早以前,燃灯佛出世时,释迦佛前世为儒童菩萨,得知燃灯佛要莅临其所在地的城池,便拿出身上仅有的五百钱从一位女子那买来了五只莲花供奉给燃灯佛。他见燃灯佛前来的路上有泥泞,便脱下自己的衣服铺上,发现未能铺满泥泞路,便再散开头发铺在地上让燃灯佛踏着头发走过。燃灯佛踏过他的头发后为他授记,预言他将成为释迦牟尼佛陀。燃灯佛语毕,儒童菩萨的身体便漂浮起来,面对燃灯佛合掌作礼。展厅中的这件《燃灯佛授记》浮雕作品保存并不完整,但儒童菩萨向妇女买花和为燃灯佛布发掩泥的关键信息却保留下来了。
此次展览的佛传故事中,《太子诞生》引人驻足。佛经记载,摩耶夫人临产回娘家,路经蓝毗尼园时感觉疲惫,于是右手扶着树枝休憩。这时释迦太子自摩耶夫人右胁下诞生(太子形象已残)。摩耶夫人左手扶着妹妹波阇波提,后者为释迦太子继母。太子前方一弓腰、手持布襟的接生者是帝释天。在波阇波提身后有两侍女,其一者左右手分别持丰饶角、水壶——丰饶角里装着谷物,寓意着丰饶、富足;画面两上角各有两身天人,其一携天鼓,天鼓的出现被认为是向世间宣示人类伟大精神导师的诞生。此外,在帝释天与摩耶夫人中间还站立一赤裸的小孩,有头光,这是诞生后的释迦太子。刚诞生的太子周行七步,步步生莲,自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整个过程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迹。画面中摩耶夫人上身裸露,身姿曼妙,肌肤极富柔弱无骨的质感,引人入胜。
释迦太子诞生后,就显现出各种不凡,并在成年后迎娶了美丽的耶输陀罗。这些过程,在众多犍陀罗美术佛传故事中以“连环画”的方式呈现。其中,《释迦太子宫廷生活与决意出家》的浮雕板颇为重要。浮雕板分上下两层,上层表现的是释迦太子成婚后的宫中生活,他斜倚在柱廊间的床上,王妃耶输陀罗坐在床边,前后左右均有乐师和侍女相伴,过着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浮雕板下层表现太子决意出家,画面是释迦太子坐在床边,耶输陀罗躺在床上,乐师和侍女们东倒西歪在地上,形容丑陋,只有释迦太子保持清醒。据《修行本起经》描述,诸神为了督促释迦太子下定出家之心,召天神乌苏慢入宫施法,使耶输陀罗及歌女皆作死人,旋即宫殿化作坟墓,太子此前所见,皆作泡影。这就是太子惊梦,也是促成其决意出家的重要原因。这两幅浮雕场景并置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象征着释迦太子放下空虚繁华的俗世生活,决心走向神圣的成佛之路。
实际上,促成释迦太子决意出家的还有另一个著名场景“树下观耕”。展厅中有一件名为《太子树下思惟》的浮雕,就是表现这一主题。太子在树下观耕时,见到虫子被小鸟啄食,感叹生命无常,由此加强了出家的决心。不过,这件《太子树下思惟》浮雕并没有雕刻牛耕地及鸟吃虫子的细节,仅表现太子半跏趺坐在台座上作思惟状,两侧有四位双手合十礼赞的天人。画外之意,需要观者自己想象。释迦太子决意出家到最后觉悟成就佛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修行——在六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维持生命的少量食物,以至于形体羸瘦,皮骨相连。这是对修行者身体和意志的巨大考验,体现了释迦佛为众生寻求解脱之道而付出的实际行动。
佛传故事中,最激动人心的当属《降魔成道》。画面中释迦面容肃穆,俨然佛陀的装束。他跏趺坐于方形的台座上,左手握衣角,右手置于右膝盖前施降魔手印,台座前有一裸形倒地者——这是被释迦佛神力打倒的魔众。在释迦佛两侧,各有一位头戴宝冠、上身裸露、腰佩宝剑的王者——这是魔王波旬,他试图拔剑伤害释迦,但被他儿子制止。在魔王两侧及上方,还有长相怪异的魔众,手持武器试图攻击释迦佛。在太子背后右侧,还有一位手持金刚杵的人物,他就是释迦佛的终身保镖执金刚神。这一剑拔弩张的场面发生在菩提树下,是释迦太子成佛前的最后考验。浮雕中的人物造型简练,动态自然,主次分明,其中人体结构和衣装雕刻样式,呈现出类型化的造型特征,这显然是源自古希腊、古罗马的雕刻技术与佛教故事题材融合后的成熟表现。
佛陀的光辉
《帝释窟禅定》是本次展览中颇为精美的一件作品。释迦太子证得佛果成为佛陀后,觉得佛法至妙,难为凡俗所知,而世人又乐生求安,好于声色,与佛道所追求的虚寂无念相去甚远,产生了舍弃众生、自我涅槃的想法,于是在帝释窟禅定。其间,帝释天、诸神前来拜访。帝释天向佛陀问法,从中得到无上喜悦。后来梵天再三劝请,佛陀听从了梵天劝请,放弃了涅槃的想法,转而以解脱众生为最终目标,开启弘法之旅。这件作品中,释迦佛跏趺坐于窟内,高肉髻,面型圆润,双目微睁,高鼻梁,嘴角内敛,表情庄严,双手施禅定手印,跏趺坐双腿向两侧外张,与上半身形成稳定的构图——洞窟外形就围绕这一构图展开。在帝释窟下方表现的是诸神,人物尺寸较小;窟两侧又有诸多同比例的天人环绕,山石树木间还有猴子、山羊、小鸟等动物,忠实再现了印度生机盎然的自然环境。其中释迦佛身形高大,占据绝对主体位置,雕刻精良,是犍陀罗佛教美术的杰作之一。
展厅中一件名为《舍卫城神变》的浮雕作品很是不凡:主尊释迦佛居于芒果树下,高肉髻,面型圆润,嘴角含笑,跏趺坐于莲座上,着袒右肩式袈裟,双手施说法手印。释迦佛左侧的是束发的弥勒菩萨,右侧是戴冠的观音菩萨,构成了标准的说法三尊像。研究者将其名为《舍卫城神变》,是认为这是表现释迦佛在舍卫城说法时发生神异事迹的简化图示。日本学者宫治昭先生指出,梵天所代表的婆罗门,与帝释天代表的刹帝利,在古代印度世界观中,处于既对立又互相补充的关系。佛教美术中的梵天和帝释天,是护卫佛陀的一对守护神,束发、提水瓶的弥勒具备“圣者、修行者的梵天性格与像容”,而敷巾冠饰的释迦、观音系则列对应帝释天,体现出“王者、战士的形象”。因此,梵天与帝释天胁侍在释迦佛两侧,意味着释迦佛的超然地位。这件作品中的释迦佛、梵天、帝释天,皆像容俊美,身体结构和肌肤质感雕刻细腻,菩萨的衣饰也恰到好处,其人物造型可谓犍陀罗美术中的标准像。
占据展厅中心位置的是一尊圆雕《佛立像》,佛像头部上扬,高肉髻,波纹发,双眼看向前上方,高鼻梁,嘴唇上有小胡髭,跣足立于方形台座上。佛像身着通肩式袈装,衣纹厚重,但并不影响佛陀健康躯体的呈现——这完全得益于成熟的古希腊雕刻技术作为支持。因此,这尊被观者称道的佛立像,是典型的“希腊化佛像”。这尊佛像头部扬起,视线上抬,与以往所见内敛、沉思的犍陀罗佛像区别明显,似乎在表达佛陀一种自信、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
此次展览的策展者罗文华老师介绍,“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自2019年启动,共花了三年时间才落地,但我们在展厅所见者,也仅仅是整个犍陀罗美术中很少的一部分。犍陀罗美术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是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明共同构筑而成的,其影响力甚至影响到现在。笔者认为,这次犍陀罗艺术展引起大众关注和热捧,其原因有三:一是犍陀罗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区域,彼时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传播产生深远影响,艺术作品更是令人着迷;二是犍陀罗美术是中国古代佛教造像最重要的源头,中国古代早期造像带有鲜明的犍陀罗造像特征,这是我们重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三是近些年对于犍陀罗美术的认识较为普及,对其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有了新的认识,现场观展成为验证观者所学所思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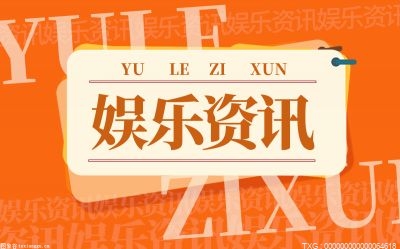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