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不任性的灵魂》收录张新颖老师15篇有关西方现当代作家的读书随笔,其中有4篇是关于博尔赫斯的。最早一篇《博尔赫斯三题》写于1991年,最近的《七个夜晚的读书人》写于2016年,篇幅都不算很长,但时间跨度却很长,首尾相隔25年。集中放在一起阅读就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奇妙感觉,可以感受作者笔力的变化,让人想起叶芝在诗里所讲述过的“随时间而来的真理”。而变化中亦有不变者存,比如喜欢用引文来编织叙事,这从《博尔赫斯三题》中已经略露端倪。又比如“迷人”的文风。在《七个夜晚的读书人》中,作者先引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证明这种迷人其实是一种自觉的追求,“迷人,正如斯蒂文森所说,是作家应该拥有的基本优点之一。舍此,别的都没用”,又接着补了一句,“倘若博尔赫斯缺乏迷人的品质,他大概就不会这么引用斯蒂文森了”。我们读完这本《不任性的灵魂》,也可以接着再补一句,倘若张新颖缺乏迷人的品质,他也就不会这么心心念念于博尔赫斯了。
在指出“迷人”这个关键词之后,作者又不动声色地拈出博尔赫斯《七夜》中所提及的两个讲演要领:第一条,要讲述“具体的事而非抽象的事”;第二条,“我并不是在跟大家讲话,而是在跟你们中的每一个人交谈”。这两条,可以视为博尔赫斯的金针度人,恰也可以视为作者自己写作的要领。
很多评论家是依靠形容词和抽象词汇在写作的,形容词用来褒贬人,抽象词汇用来唬弄人,以此为背景,方可感知上述两条要领的可贵。这些年读张新颖老师的文章,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文字能够句句落到具体的实处,用流行的俗语来说,就是“干货”很多,同时文字的起承转合又很熨帖自然,甚至是若有若无的,看起来只是一段一段引文的缀合,没有什么文章架子。这样的文章,似易实难,非要等到自己写的时候才能体会。同时,这样的文章又很耐读,其中那些引文和作者自己的文字之间能够达至某种水乳交融的效果——他能让引文也成为一种亲切的交谈,而非贴附在文章表面的光鲜亮丽的瓷砖。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开头谈及凯尔特人的信仰:“他们相信,我们的亲人死去之后,灵魂会被拘禁在一些下等物种的躯壳内,例如一头野兽,一株草木,或者一件无生物,将成为他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确实以为他们已死,直到有一天——不少人碰不到这一天——我们赶巧经过某一棵树,而树里偏偏拘禁着他们的灵魂。于是灵魂颤动起来,呼唤我们,我们倘若听到他们的叫唤,禁术也就随之破解。他们的灵魂得以解脱,他们战胜了死亡,又回来同我们一起生活。”
读书人,也可以视为一直在倾听过往灵魂呼唤的人。他从一本本不同时代不同国族的书籍中找到并唤醒一些文句,令它们摆脱被拘禁在书架上的命运,让它们得以同此时此地的我们一起重新生活。要从一起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张新颖对于引文的迷恋,而我们读他的著作,也是在参与这种由他所努力唤起的跨越时空的共同生活。
他称赞《日瓦戈医生》是“一部捍卫生活的书”;强调雷蒙德·卡佛“写这些被生活淹没了的人”本身也是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指出在E.B.怀特的“文体和生活之间,好像有一个通道”;借助奥登对于歌德的理解,讲述承担生活的责任之于艺术家的重要性。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对张新颖老师而言,生活的要领一如写作的要领,都是具体的,都是在和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事的交流中所完成的。正如他引用帕斯捷尔纳克对契诃夫的称赞,“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
在《俄国之恋》这篇文章中,张新颖讲述以赛亚·伯林对于阿赫玛托娃的认同,“她熟悉的每一个人他都熟悉,她读过的每一本书他都读过,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层含义他都懂得”。而我在读这本《不任性的灵魂》时,时常也会生出相似的感受。这本书里所谈到的那些作家,布罗茨基、奥登、艾略特、以赛亚·伯林、博尔赫斯、卡佛、怀特……几乎也都是我所热爱的作家;而他在书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层含义,我也自认为是懂得并且深深认可的。在思南读书会的分享现场,以赛亚·伯林说,在经历过2022年的一切之后,这本他原先拖延犹豫的书成为他如今迫切想出版的书。“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那些他笔下提及的不任性的灵魂,克制而诚恳,宽阔而自由,连同他本人一起,会是如晦的风雨中令人安心的存在。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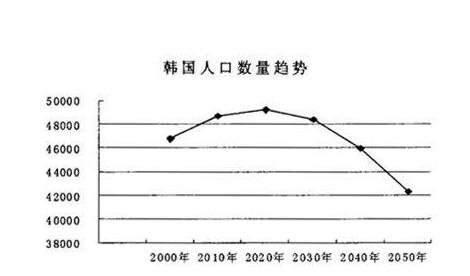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