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开年,一部以“中国妖怪”为题材的动画短片《中国奇谭》意外出圈,引发关注。目前已经播出的四集风格各异,无论是讽喻当代“职场社畜生活”,还是在诡谲的“套娃”故事中探讨人心多变难测,不少观众称从中看到了“不一样的妖”。这部作品目前的播放量也超过5000万次,一时之间,所谓“奇谭”的确在开年伊始贡献了不少谈资。
不过,随着关注度上升,这部主打“妖怪”背景的作品也难逃争议。有家长在某平台发文称,孩子被其中的妖怪形象吓哭了,甚至上升到了“童年阴影”的程度。该言论一出随即在互联网引发讨论,不少网友逐条予以反驳。而透过意见分裂的舆论场,我们再度依稀看到妖怪在大众心目中隐秘留存的刻板印象。
多年前,自称“搜神馆主”的妖怪爱好者张云就觉察到了这一现象。出生在安徽乡村的他自小便浸润在邻里间口耳相传的妖怪故事中,雾气笼罩下的那个世界虚幻而又真实,他至今想起时,亦能复刻出讲述者“老神在在”的语调,被人与妖之间互为镜像的羁绊所吸引。然而即便如此,不少人在听闻这些故事时,依然面露猜疑甚至不乏鄙夷,觉得是“封建迷信”,且家喻户晓的那些妖怪题材作品也多将之刻画为面目狰狞的骇人形象。而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妖怪学”却早在两百年前便生根发芽,从民间到学界不断丰富着相关内容,甚至成为IP产生了走出国门的影响力,尽管其中70%的妖怪都来自于中国。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于是,张云试图回到历史典籍中,去看看那些中国传统中的妖怪故事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于大众认知,传统的妖怪大多与人为善,它们存在于人与世界的裂隙当中,是当时人们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妖怪后来又是如何逐渐成了需要降伏的对象?当人们恐惧妖怪时,恐惧的又是什么?从这一点而言,张云坦言《中国奇谭》出圈背后,更重要的其实是能够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妖”。
这些年,张云也在进行妖怪题材类的创作改编,从妖怪与推理悬疑结合的《猫怪》,到治愈系风格的故事集《妖怪奇谭》,尝试呈现更立体,大众接受度更高的妖怪形象。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张云,从《中国奇谭》延伸出的话题聊起,进而谈到妖怪在国内的刻板印象,它又如何在历史进程中逐渐被异化,被客体化。而随着妖怪题材的兴起,当大众的新奇褪去后,以妖怪为主人公的创作如何才能避免流于“人类故事”的复制?或许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奇谭》更多意味着一种开始。
都在谈妖怪,什么是妖怪?
新京报:目前《中国奇谭》在豆瓣获得了超九万人评价,评分也达到了9.4分(截至1月15日)。我很好奇,在观众身份之外,作为“妖怪学”的研究者,你在看这部片子时会有怎样的感受,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张云:它的题材是最吸引我的。印象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天书奇谭》播出,那时妖怪类的创作还比较多,但是后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在荧幕中看到的妖怪几乎很少。虽然这之间也出现过类似《捉妖记》之类的影片,但其中关于妖怪的部分,比如胡巴,其实和中国传统中的妖怪已经没有多大联系了,更多是创作者的构思。这次《中国奇谭》主打妖怪这个题材,而且是从中国传统中生发出来,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我刚看完“小妖怪的夏天”这集,个人是比较喜欢的。这个故事放置在《西游记》的大背景下,但并没有从常见的“取经”的视角,或者“降妖伏魔”的视角去展开,而是围绕一个无名的、最底层的小妖怪去搭建这个故事,观众很容易带入。而且,它在不断和镇上的人发生关系,从真实的生活里走过,这里恰恰是最符合中国妖怪传统的地方,妖怪和人的日常生活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新京报:这集结尾部分的“反转”耐人寻味,大圣没有真的打死小猪妖,还给了它三根毫毛自保。
张云:说到这,我个人其实更喜欢“反转”之前那个结局,就停留在小猪妖被不由分说给了当头一棒那里,后面的“反转”看得出,是有意想满足“大团圆”式结局的期待。但从中国妖怪传统来看,第一个结局是很真实的,中国的妖怪一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典籍中记载的绝大多数妖怪在与人相处时,要么是被人除掉了,要么就是很伤心地离开了。在儒家所谓的正统看来,那些“怪异”的,不被承认的,最后的结局往往都是被消灭了。当然,“反转”后的温暖也无可厚非,两个结局都各有其深意吧。
新京报:通过这部动画,不少网友称“看到了不一样的妖”。这也侧面反映出,许多观众是以这部作品为契机开始去接触不带“滤镜”的妖怪。而说起“妖怪”,很长时间里人们会将“妖精鬼怪”连用,你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对此做过辨析,可否再和读者分享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
张云:“妖怪”一词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在天命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后,汉朝董仲舒在古代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灾异说”等思想。他指出天与人相感应, 君主有德天降祥瑞,君主失德天降灾异。在古代,常常把一些当时知识水平不能理解的反常现象、自然灾害等视为“妖怪”。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妖怪是各种灾异之统称。比如《左传》中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第一次对妖怪进行精确定义的,是东晋的干宝。干宝在《搜神记》中明确提出:“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貌、言、视、听、思),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干宝认为,妖怪是阴阳元气所依附的物体,因为元气在物体内紊乱,发生了变异,物体放在外形上也发生了变化。形神气质,是外表和内在这两种要素在物体上的作用体现,它们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为本源,与容貌、言谈、观察、聆听、思考五种事情相联系。虽然它们消灭、增长、上升、下降,变化多端,但它们在祸福的征兆上,都可在一定的范围内加以论定。
在这个基础上,干宝进一步提出,依附在物体上的精气在体内混乱会使得物体的外形发生改变,从而变成妖怪。妖怪的本源是“五行”,又与“五事”密切相关,具有祸福上的征兆意义。
妖怪可以分为:妖、精、鬼、怪。人之假造则为妖,那些人所化成或者动物以人形呈现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妖”,比如《鹅鹅鹅》中的兔妖、狐妖。而物之性灵为精,它们往往由山石、植物、动物(不以人的形象出现)、器物等所化,所以《苍兰诀》里的小兰花又被喊作“兰花精”,而不是“兰花妖”,这倒不是说因为她出身仙界。所谓“鬼”,指的是魂不散者,以幽灵、魂魄、亡像出现,比如画皮。最后,物之异常则为“怪”,它是说那些对人而言不了解,平常生活里没见过的事物,或者即便见过同类,它们也和同类相比有很大差别的,比如传闻中能吞象的巴蛇。
新京报:在这部动画的先导片中,主创们曾打出“什么是奇谭”的设问,常出现在妖怪故事集名称中的“奇谭”一词是出自何处,它和“志怪”“志异”“物语”等说法有不同的侧重吗?
张云:在谈“奇谭”之前,我们先聊聊“志怪”。其实提起妖怪,“志怪”一词不可不提,它最早出自《庄子》,《逍遥游》曰:“齐谐者,志怪者也。”《释文》中也有言:“志怪:志,记也;怪,异也。”尽管经过发展,后世将“志怪”视之为一种文体,但在先秦时期,志怪是一个动词性词组,指记载怪异的事物。严格来说,妖怪的历史要比“志怪”长,早在文字还没有创造出来时,妖怪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幼年期的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研究妖怪主要依靠“志怪”的记录,“志怪”和“志异”本质上是一回事。
“物语”这个词常见于日本文学中,它大致产生于公元十世纪初年的平安时代,是在日本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且也受到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我们大概都或多或少听过《源氏物语》,而在《源氏物语》之前,物语文学其实分为两个流派,一种是创作物语,如《竹取物语》《落洼物语》,这种类型的物语文学内容一般是虚构的,具有传奇色彩,另外一类为歌物语,如《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以和歌为主,大多属于客观叙事或历史记述。在此基础上,日本又产生了所谓的百物语。
说到百物语,它是日本民间的一种习俗,大约兴起于江户时代,是一种集体召唤妖怪的游戏,多半发生在夏天的夜晚。传说只要点100支蜡烛,说完一个怪谈吹熄一支蜡烛,直到说完100个怪谈,蜡烛全部吹熄之时,妖怪就会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百物语”才成了如今怪谈文学的代名词。
最后说说“奇谭”,其实这个词等同于“奇谈”,偏向于指那些令人觉得奇怪的言论或见解,相比之下,这个说法会更现代一些。总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志怪、志异,更偏向于写实,对来源于生活中的这些事物的记载,真实性较高,而奇谭和物语,艺术创造、虚构性多一点。这是一个大的区别。
妖怪存在于人心和世界的缝隙中
新京报:目前播出的头两集《小妖怪的夏天》和《鹅鹅鹅》都不失为在传统故事基础上所作的改编。前者设定中的世界观承接了《西游记》,后者则出自南朝梁时吴均流传下来的《续齐谐记》中的“阳羡鹅笼”,可否展开讲讲片中的设定伏笔与具体史料之间的联系?
张云:本质上,的确算是“新瓶装旧酒”的尝试,根基在古代典籍,但是用现代的手法、眼光和现代人的思维去演绎故事,反映的是现代人的世界观。其实,历朝历代的志怪大都如此,记录着当时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存状态。
《西游记》耳熟能详,无需多言,简单谈谈“阳羡鹅笼”这个故事吧。这则故事出自南朝梁时吴均流传下来的《续齐谐记》,讲一个年轻货郎在山里偶遇一个受伤书生,书生请货郎喝酒,席间寡淡,于是从嘴里请出一位女子,后来书生睡着后,女子又复从口中请出另一位心上人。就其内核而言,如今我们可能会说它是一个常见的“套娃”,而在当时人看来,它其实是记录了件“怪事”,可能不见得是妖怪,而是奇人轶事,他们嘴里能吞剑,能藏很多奇怪的东西,这里是有其传统的。
另外从叙事结构来说,镜像嵌套在妖怪故事中相当典型。比如典籍中还记载有一个叫“镜目”的妖怪,传说一个人在夜晚独行,偶然发现道路前方有一个人影,心中大喜终于遇到一个同伴,于是上前拍他的肩膀,只见那人扭过头时双目圆睁,面容骇人,两眼像镜子一样灼灼放光,才知是个妖怪。这个人连忙往回跑,气喘吁吁时又遇一个人影,他长吁一口气说:“今天终于逃过一劫,刚刚那妖怪太吓人了。”人影转身说:“你看是我这个样子吗?”原来还是之前那个妖怪!
新京报:这类“套娃”或“镜像”后劲儿很足。豆瓣有网友称“从猎奇的入口进入,原以为奇谭几许,不过文人散心之作。纵身其间,才知道中国哲学尽在志怪笔记之中。”纪晓岚也曾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认为“阳羡鹅笼”乃“幻中出幻,辗转相生”。这种哲学意味的渗透在中国妖怪故事中是一种传统吗?
张云:中国妖怪故事典籍众多,包罗万象,哲学意味是完全有的。且妖怪故事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世界,对自然,对社会,甚至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思考,而创作者又大多是饱学之士,哲学思考是自然而然的。比如说,人与自然及万物到底应该如何相处,其实古代的人想法很明了。比如《广异记》中记有山魈这么一个妖怪,原文是:
“山魈者,独足反踵,手足三歧。每岁中与人营田,人出田及种,余耕地种植,并是山魈,谷熟则来唤人平分。性质直,与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这个妖怪的特性是,它和人相处非常融洽,深山老林中生活的人耕种成本很高,于是他们定下约定,人提供种子,山魈负责耕种,待谷物成熟后五五平分,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这其中渗透出的其实是人地合而为一,均衡和谐的相处之道,而这种对人地关系的理解在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我很喜欢这个妖怪,喜欢这种思考,所以把它重新创作,写入了《妖怪奇谭》中。
此外,除了哲学思考,中国妖怪故事中还有其他的文化价值,比如有些古代典籍中的记载会让人觉得我们的老祖先们“科学范”十足!唐代《酉阳杂俎》中记载一个名为“修月人”的妖怪,它介绍自己说:“月亮的情况像圆球,它的阴影多半是因为太阳光被遮蔽才产生的,在它的暗处,常常有八万二千人在那里修月,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中不难看出,对月食的理解早在唐代就带有些科学意味了。
新京报:片中的妖怪形象也给不少网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被家族寄予厚望的“打工仔”小猪妖,操心儿子不爱喝水的猪妈妈,再到心上人并非视其为意中人的狐狸书生,这些妖怪形象更为立体。在“不一样的妖”感叹背后,长期以来,大众对妖怪的认知都存在哪些刻板印象?
张云:我觉得一个最大的误解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提到妖怪,就觉得是封建迷信。其实妖怪存在于人心和世界的缝隙之中,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或者说妖怪反映的,恰恰是人深层次的精神世界。妖怪学在日本有更为体系化的发展,这与妖怪文化的意义在日本有相当高的认可度有很大关系,日本妖怪研究专家小松和彦教授曾经说,通过妖怪的研究,可以探究日本社会文化和宇宙观的变迁史,揭示出背后不变的日本人的固有信仰,以及区分自我与他者的精神结构。而国内在这一点的认知上至今没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这种情况也与妖怪的定义相对模糊有关,很多人其实分不太清到底什么是妖怪。首先,神不是妖怪,正如小松和彦不同意柳田国男所认为的妖怪是衰退的神灵一样,中国神灵众多,从原始社会时期的天神崇拜、自然崇拜、万物有灵思想到本土宗教产生出来的神尊,再到佛教等宗教传播后出现的神灵形象,何止万千,相关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这些不属于妖怪的范畴。当然,原本是妖怪,但后来升格为神,或者被视为神的不在此列。其次,异人不是妖怪。中国历代典籍中关于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羽化成仙的异人的描述极多,此类应该排除于妖怪之外。再有就是,“异象”也不是妖怪。典籍中记载的诸如“人生三臂”“狗两头”等等的众多偶然的异象,虽怪异,但不属于妖怪的范畴之内。
值得一提的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说《捉妖记》中的胡巴与中国妖怪传统较远,是因为这属于作者个人创造、主观臆想的。这一点上,《西游记》中的所谓的妖怪其实严格意义上也都不属于“妖怪”范畴。
由于很多我们自小接触的“妖怪”类题材的作品中,妖怪的形象几乎都是面目狰狞的,这也使得很多人一提妖怪,就觉得恐怖,也就谈不上去深入了解或是用心感受。其实中国绝大多数的妖怪是与人为善的,是温暖的。当然很吓人的妖怪也有,但占比很小。此外,还有人误将中国的妖怪误认为是日本的,我去过几次动漫展,几个扮作妖怪的动漫爱好者也会误认为姑获鸟这种是日本妖怪。
新京报:这部片子引发的另一个讨论是,不少网友亦称,从中看到了一种所谓的“中式幽默与诡谲”。我们知道日本也有不少与妖怪有关的文学或影视创作,诸如《千与千寻》《夏目友人帐》等,据你的研究观察,中国的妖怪故事与日本的妖怪故事各有哪些侧重?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种“中国式妖怪”(或者说“中式妖怪故事”)的特点?
张云:不管是中国妖怪故事,还是日本妖怪故事,都是当时人们对于世界、社会、自然、人生的思考。既然是这样,肯定和各自的文化特性、民族特性密切相关。但妖怪的源头在中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两者相比,当然也有一定的区别。
具体而言,中国妖怪故事历史很长,我们讲说“万年妖怪”,这并非夸张,关于妖怪的典籍众多;另外,日本的妖怪,大多其实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相较而言,中国妖怪的种类或者说类型要更丰富,不论是先秦时期那种具备磅礴气象,“开天辟地”的大型妖怪,比如混沌、穷奇、梼杌等,还是说民间口耳相传,带着浓浓人间烟火气的妖怪、物怪,种类很丰富。而且如果你去典籍中细看会发现,中国的妖怪禀性丰腴,嬉笑怒骂,各种都有,但日本的妖怪,总体风格上,大部分是冰冷的,是幽怨的甚至是复仇的。
为什么一提妖怪,就觉得需要“降伏”?
新京报:2020年,你从数百部古籍中搜集整理上千个妖怪,编写了《中国妖怪故事》一书。你也反复提到,妖怪对古人来说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理解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你怎么理解关于妖怪叙事中这种人与妖的牵绊?
张云:其实人和妖,本质而言没什么不同,或者说,妖怪就是人的另一张脸。《左传》中有记载,“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妖由人兴”。追根溯源,妖怪的产生,根子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价值判断。“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事物的存在,建立在一种内外和谐的稳定状态,但是有些时候如果发生了变异,就会背离人类的正常认知和社会评价标准,也就是说站在了对立面,失去了“常性”,在古人眼里,便成了妖怪。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中国的大多数妖怪其实是与人为善的,且它们曾是先民对不可解现象的一种理解的尝试。那么,妖怪后来究竟是如何逐渐成了需要“降伏”的对象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指向延续至今,甚至于今天的词汇库中仍然有“作妖”这样的说法。
张云:的确,回看典籍我们会发现,人类一开始去记载妖怪,和妖怪发生互动,是有一个现实的生活基础的,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尝试认识自然,甚至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黄帝时期的《白泽图》便是这样,传闻白泽将天下的一万多种妖怪记录在册,并详细描述了妖怪的形象,人应该如何与其相处,如何不为其所伤害的应对方法等,一直流传至宋代方消失。这是一个传统,很长时间里古代人并不觉得妖怪是虚幻的,认为妖怪与人没什么不同,人与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当中,更谈不上要消灭对方。
而这种转变的发生,恰与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化进程几乎同步。儒家认为社会运行有其正常的标准,它应当是正统、常规且可控的,因而《左传》中会不断讲“反物为妖”,将那些游离于正常标准之外的都笼统划入“妖”的范畴。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妖怪意味着异类,而异类意味着对立,对立招致的即是敌意。
话说回来,记有妖怪的典籍大多是古代文人所著,他们难免浸润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考虑到它的传播性,如何去写一个结局就很值得玩味了。我在读典籍中的妖怪故事时经常会发现,从前半部分的笔触中能明显感觉到,作者本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妖怪的,但最后不得已将落点引到妖怪被除掉了。大多都故事很精彩,结尾很潦草。“怪遂绝”,全剧终。
新京报:两年前你做妖怪故事的整理编纂时,国内几乎少有人同行。这两年,“妖怪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哪些新的进展吗?
张云:进程其实要比预想中快很多。两年前,我在做的算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事情,先从典籍中把妖怪相关的部分整理出来,至少让大家能集中看到中国的妖怪有多少种,分别是怎样记载的,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只是这样还不够。传统典籍中的妖怪故事大多篇幅较短,很多故事可能也不符合今天人们的阅读偏好,考虑的重心也逐渐转向怎么能让大家更好地接纳这个东西。而这两年能明显感觉到,关于妖怪题材的作品开始大量进入公众视线了。
至于学界,对于妖怪作为一种民俗研究范畴的关注度也有所上升,不少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有待商榷,但我的一个观察是,我们对妖怪的研究可能还需要一个更加整体、全局、或者说更综合的视野,从“中国妖怪”的宏观视角去研究,从而建立起“中国妖怪学”的框架,而不是仅仅将目光放在中国某个地区或者某少数民族内部的民间妖怪形象研究,又或者是历史上某个短时期内的妖怪特点,比较碎片化,缺少一些脉络感。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比较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妖怪题材兴起:找回失落已久的质疑传统
新京报:日本在“妖怪学”方面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也与民间的自发支持,以及各界持续的创作兴趣息息相关。近年来,在普及推广中国的“妖怪学”之外,你也在尝试不同的妖怪故事创作。从妖怪与推理悬疑结合的《猫怪》,到治愈系风格的故事集《妖怪奇谭》。同为创作者,据你的观察,《中国奇谭》出圈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以及由此引出的是,在今天什么样的妖怪故事可能是更打动人的?
张云:我觉得这当中最难得的是从继承性出发,所衍生出的那种现代感吧。这种交融渗透在许多方面,单从视觉上来说,上美影厂之前的动画,大多都偏古典,比如“小蝌蚪找妈妈”之类,是通过水墨画去晕染一种国风,而这次这部动画,你会发现它虽然也是国风的,但是这种画面处理其实比较贴近现代人的审美。此外,包括它故事呈现的内容,以及有些现代感的语言带来的与观众之间的互动感,这些都容易拉近距离。真正打动人的妖怪故事,大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不杜撰,不虚构,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的价值观,去照鉴我们的生活。话说回来,当然可以与“当下”走得近,这没问题,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太过功利。
新京报:《妖怪奇谭》中,“空之衣”的故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混沌凿七窍的传统架构中,你尝试赋予了它行为的动机,何以成为“混沌”又为何想要走出混沌,其间透着一股拆解与反叛的原生力量。这个故事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张云:混沌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妖怪。起初读到关于它的记载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妖怪的很多行为都和人们的认知是相悖的,它有种没有来由的叛逆,凡是世人认为是好的,它就唾弃,凡是被公认为是恶的,它就欢喜。但真的会有天生“不分善恶”的存在吗?这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包括后来读黄帝和蚩尤大战的记载,蚩尤穷凶极恶,而黄帝则是非常公正英明,这种两极化的放大太过泾渭分明,而在那些普世的价值之外,是非真的是我们被告诉的那样吗?这些疑惑越积越多,于是慢慢有了将混沌和蚩尤进行串联的故事架构。
新京报:这个故事末尾其实也有“反转”。起初,混沌希望拥有一双眼睛,为了记住旧友蚩尤的面貌,后来,白泽道破,它不愿忘记蚩尤,不是因为那是它的挚友,而是因为它还在执着。混沌又问,“我都是非不分了,还有什么可执着”。白泽说:“其实长久的是非不分,本身就是执着。”
张云:是的,话语权一直都掌握在胜利者的一侧,混沌或许也曾经做过些无法被收编的事,从而被划入了“不分善恶”的阵营,久到它可能自己都忘记了,刻意“是非不分”的前提恰恰是心里非常清楚孰是孰非。总体上,混沌的形象和性格都还是典籍中记载的那样,但我想做的,是通过想象填补它形象形成之前的那块空白,想要弄明白究竟“为什么”。
新京报:在人的世界之外,与妖怪世界相对的往往是一个被人为升格的“仙界”。有趣的是,这几年“为妖怪正名”似乎暗合了某种时代的集体情绪。比如“小妖怪的夏天”中对“大圣”传统形象的突破,尽管结局有反转,但大圣出场之时的确不由分说给了小猪妖当头一棒。另外包括一些影视剧中,比如前不久的《苍兰诀》《月歌行》等,传统意义上所谓“仙界”的正面形象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颠覆。这是否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妖怪文化?你会怎么看最近这些年这种叙事风向上的转变?
张云:的确是这样,这算是近几年的一个“破局”吧。妖怪形象本身也带有一股子反叛的劲头,不管是面对神仙还是天师法师,哪怕我能力弱小,为了我的原则,为了我的生存,我可以勇敢地反抗。这种特性,特别令人感动。
其实在妖怪故事的记载中,这种“颠覆”是有它的传统的,只不过可能慢慢地,逐渐被我们遗忘了吧。我印象中有一个故事,它讲书生和一个妖怪结缘,家人得知后就禁足了书生,还找了一个道士。按照“常规”逻辑,道士是来除妖的,结果道士听完事情经过后把那个妖怪找来,他觉得这段姻缘很好,反手撮合促成了这对儿。古人的记载里藏有很深的质疑传统在。包括从这几年社会整个大环境来看,这种质疑和批判思维的确在复兴。在读到书中白纸黑字的论断时,我们是否敢于提出不同的声音,“觉得蚩尤也许不是这样”?
新京报:随着妖怪题材的兴起,可能需要追问的是,在“妖怪”的外壳下,不论我们之后是选择去现象式的刻画当下社会生活百态,比如“职场社畜”现状;还是说,借由妖怪去挖掘那些更为深层次的治愈性的力量,当故事的内核相似时,妖怪的题材能够为整体的叙事带来哪些拓展空间?换言之,如果这些故事也可以发生在真实的人之间,那么当观众的新奇感褪去,以妖怪为主人公的讲述如何才能避免流于“换汤不换药”的尴尬与惰性?
张云:这的确是在“妖怪”题材的热度上来后,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人和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局限性,受特定时空的限制,也难免有七情六欲,乃至常规逻辑的束缚。但“妖怪”题材能够提供的恰是一片无限解放束缚的想象空间,不单单局限在现实层面的议题,而是对那些时代深处的情绪和问题有更敏锐的触角,甚至有时候能提供一种预见性的洞察,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我个人的写作感受而言,妖怪题材还给我一种很深的历史支撑感,关于妖怪故事的传统其实是我们在创作时能够保证“风筝不断”的那根线。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是会觉得《鹅鹅鹅》这样的创作是耐人寻味的?前人志怪中展示的那种对人性的洞察,对裂隙的捕捉,这些都在夯实着今天妖怪题材创作的厚度,而其中精华的部分应该也值得被越来越多人看到。
张云,安徽灵璧人。作家、记者、编剧。自号“搜神馆主”,喜诡异野史,民间怪谈。著有《中国妖怪故事(全集)》《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妖怪奇谭》《猫怪》等。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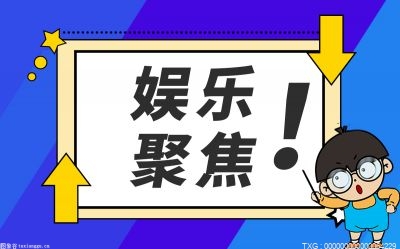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