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中日两国自古隔海相望,地理上的天然优势使得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公元前3世纪便已开始,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间绵延不绝。日前,由清华大学和日本奈良县联合举办“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特展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品既有来自奈良的100余件(套)与中国相关的文物,又有国内机构所藏数十件与日本相关文物。
日本绳纹时代(日本石器时代后期)和弥生时代(上承绳纹时代,下启古坟时代)遗留下的拙朴陶器,刻画有鸟装人物纹、楼阁纹、建筑物与鹿纹等,描绘了其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祭祀场景。而自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大量中国铜镜传入日本,且深受喜爱并被仿制,这些仿制镜在纹样和铭文上有所简化或变动,在尺寸或造型上亦有自我创新,比如带着五个铃铛的铜镜,其功能已非照容、装饰,而是用于祭祀。
日本的国宝、古坟时代的七支刀,则是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文化交流的物证。七支刀的造型奇特不凡,刀身嵌有错金铭文,以中国的年号纪年,记载了百济王世子制造七支刀送给倭王之事,证明了日本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来往联系。此外,履和鞍的金属部件上的龟甲系纹与棕榈叶纹也许与中国乃至西亚有着联系。使用金铜材质、复杂纹样和镶嵌工艺制造的华丽马具,与十六国时期前燕的透雕鎏金铜马具饰件对照观之,令人遐思。不难想象,来自中国北方的马背文化和西亚的艺术,也许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交会融合,再传往大海彼岸的岛屿。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进入黄金时代,为了学习中国文化,自7世纪初至9世纪末期间,日本四次遣使入隋、十余次遣使入唐,热情吸收中华文明,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文化交流高潮。
日本史上首个正式都城——藤原京位于奈良境内。而接下来的都城平城京,亦在奈良。因此,奈良不仅是古代日本文明发源地,而且在公元794年朝廷迁都平安京(今京都)之前,一直都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使得奈良成为中日文化交融的结晶与象征。
奈良时代的日本吸收了大量中国唐朝的文化和制度。平城京的格局模仿的是唐长安城,其规模相当于后者的四分之一。典籍、文学、服饰、器具也在这一时期源源不断从中国传入日本,来到奈良。一时之间,“唐风洋溢奈良城”。砖佛由玄奘法师自印度求法归来时带到长安,遣唐使将这项技艺带回日本传播开去。法隆寺金堂壁画是初唐时期的壁画样式。高松塚古坟中所绘的四神和人物壁画,皆是隋唐古墓壁画常见题材。西壁女子群像所运用的透视法,与唐代懿德太子墓中壁画技法相同。唐代盛行的著名陶器唐三彩也传入日本,日本国内还据此模仿生产了奈良三彩。
在遣唐使的时代,人们把遣唐使带回日本、由朝廷负责管理和再分配的物品称为“唐物”。这些为日本各阶层所喜爱和追求的乐器、瓷器、书画、香料、家具等精美物品,除了来自唐朝,也有来自朝鲜半岛和其他地区,但由于唐朝的影响力实在过于巨大,乃至于它们被统称为“唐物”,这一名词在日本文化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禅宗七祖菏泽神会墓中出土的一件唐代鎏金青铜柄香炉,炉柄尾端下折向外,上有一只瑞兽蹲坐在莲花座上。在保存了大量唐代精美器物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有紫檀金钿柄香炉、白铜柄香炉、赤铜柄香炉和黄铜柄香炉各一件,皆有长柄和蹲坐在莲花座上的瑞兽,与神会墓中香炉的形制十分相像,佐证了唐物在日本之受尊崇。
奈良一直流传着鉴真东渡的动人故事,长安也曾留下阿倍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储光羲等交往的身影。鉴真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历经千余年风雨洗礼,盛唐风韵依然不减。唐诗中诸多送日本友人的美好诗篇,在中华大地传诵。历史遗存见证了中日两国的文明演进和不可磨灭的往来痕迹。
回望奈良,千余年前的汉唐繁华闪现。文化和文明之美不仅跨越国界,也跨越时代,滋养后来人。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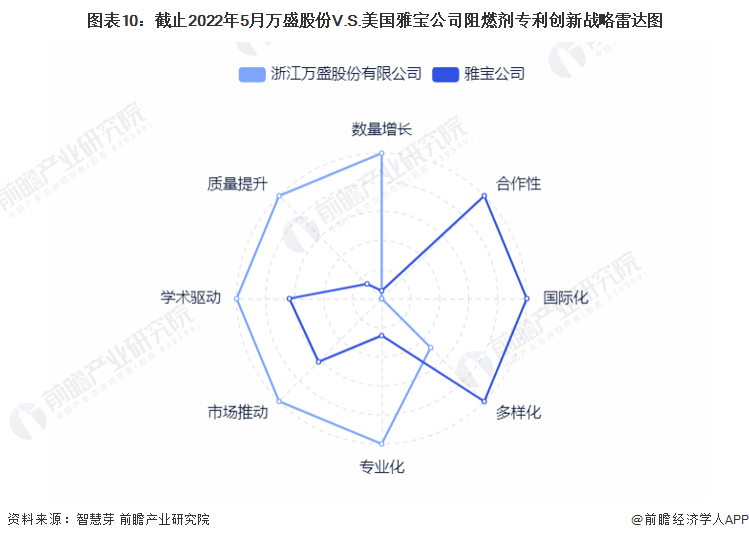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