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上月月底,备受瞩目的影片《金发梦露》(Blonde)登陆流媒体网飞,影片早前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被多家媒体预测为夺奖大热门,但该片随后在评奖中颗粒无收,还收获了不小的争议。在英语评分网站Metacritic上,各家媒体给出了从40到90不等的分数,令人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影片能让观众有如此分裂的体验。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影片由新西兰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执导,改编自女性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同名虚构作品。原书受到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星之一、上世纪50年代“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生平经历的启发,但欧茨坚称该书是“虚构而非传记”。虽然如此,书中的诸多情节在现实中依旧有迹可循,毕竟玛丽莲·梦露曾经真实存在于美国历史之中,而无论是她与身边男性的关系(书中往往将他们的姓名模糊化处理)、其最终的悲剧性命运抑或是她对美国社会及电影历史造成的影响,都让这部作品充满浓重的、无法剥离的现实指涉。
玛丽莲·梦露的出现与美国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上步入二战之后的黄金时期,电影产业也在战后经济的浪潮中乘势而上。为了将更多男性观众引入电影院,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发动完善的造星机器,创造出“玛丽莲·梦露”这个明星形象,用以取代上世纪40年代为取悦女性观众而精心打造的一批聪慧、睿智的女星形象。
应该说,梦露作为一个颇具性意味的形象,从其出现、发展到悲剧性的终结,很大程度上都是男性凝视的结果。电影《金发梦露》的整个创作很大程度上便是基于这一论断,然而比较矛盾的是,似乎是为了达成某种虚构性和寓言性,影片在有意无意之间采用一种“去历史化”书写方式:只有属于历史的服化道,真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观念却付之阙如。
很多创作者都善于将人物放入到历史语境当中,比如托德·海因斯就在《远离天堂》和《卡罗尔》里构建了一个不仅在视觉层面,更在精神层面可信的上世纪50年代,让我们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女性在美国社会里的痛苦挣扎,理解她们想要超越社会礼俗、对女性的规训却无法实现的悲情状况。
与此相反,《金发梦露》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价值或氛围极少直接呈现,而且对原书中比较核心的部分,亦即玛丽莲·梦露极具历史典型性的内心独白也进行了许多无谓的删减,只是讨巧地将梦露表述为一个半吊子“契诃夫式”(多次引用强调)的、想要逃离却永远无法逃离的、刻板的“悲剧人物”:种种无法自我实现和外界强加给她的属性,让她内心充满无可奈何的不满。至于她到底怎样无法实现自我,对于男性目光又有着怎样的矛盾心态,空壳一样的“梦露”给不出切实完整的答案。
对多米尼克来说,人物似乎根本不需要什么主体性。女主人公自人生之初即开始不断被各种男性施加迫害,导致她在不断强暴、流产、漠视的死循环中精神分裂,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梦露看似是主人公,其实无需与周围任何人有任何实质性的关系,只消做一名彻头彻尾的“受害者”,便可以轻松走向历史中的结局。至于她的婚姻、工作、生活到底怎样让她走向毁灭?其中有着怎样细微的转变和复杂的情愫?我们看电影之前不甚清楚,看之后仍然不甚清楚。《金发梦露》给人的感觉并不比八卦小报、自媒体的文章高明,无数角色像跑马灯一样从梦露的周围擦身而过,既没有与她产生过刻骨铭心的情感,也没有产生过任何精神层面的连接。最终,“梦露之死”被简化成一份乏味的提纲,甚至更糟,可以被认为是遗传性精神疾病的宿命(影片也含糊其辞地有意往这个方向引导)。
当然从这个角度上看,多米尼克也不只对主角漠不关心,为了个人风格的挥洒,他可以牺牲掉所有角色。影片懒得为任何人赋予个性,男女平等,所有人都是纸片。最终的结果是,影片里的所有演员都被无止境地剥削,不管(她)他们多用力地塑造、扮演、控制面部表情,最后都会被多米尼克搅成一坨谈不上任何层次的浆糊:玛丽莲·梦露从头到尾都在哭,“作家”(原型是阿瑟·米勒)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梦露身上发生了什么,最滑稽的还是“总统”(原型是肯尼迪),原著中的几个章节压缩成了几分钟,被简笔勾画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
我们来不及了解梦露与肯尼迪出任总统之前就开始的恋情,来不及明白权势怎样腐蚀情感,更来不及知道梦露如何自处;影片甚至没有给观众留出恨他的时间,剩下的只有漫画式的呻吟。应该说,《金发梦露》极其生动地从反面揭示了无论调度有多么花哨,剪辑有多么酷炫,如果不具体地展现一个人,就没有办法接近角色,更没有办法让观众切身理解她的处境。
这里可以再提一句,玛丽莲·梦露真实的死因确实是服药过量,但是这背后有其复杂的成因,包括严重的抑郁以及其他多种生理疾病,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好莱坞电影产业“看不见的手”对女性身体和精神无止境的剥削、利用乃至抛弃,但影片却对系统性的问题完全忽视。现实中的梦露与周围人的关系也并没有片中表现的那么粗暴简单,比如她与前夫乔·迪马乔(片中不具名的“前运动员”)的关系就远比片中呈现的复杂,而她本人也曾经为支持阿瑟·米勒而受到好莱坞猎巫运动的波及。这些足以增加人物厚度的可能性,多米尼克同样置之不理。
与这种漠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米尼克对模拟所谓梦露精神世界的热衷。导演总是希望透过快速闪回、GoPro镜头、扭曲的浅景深画面等种种手段将角色内心的痛苦、焦虑、幻象表达出来,且不提这些花里胡哨的手法是否可以形成统一的美学风格,单说这些手法是否真能服务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构建,都让人不得不画个问号。
《金发梦露》很难不让人想起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的作品《第一夫人》,因为前者可能确实在片中狡猾地致敬了一下后者——镜头在掩面而泣的杰奎琳·肯尼迪面前一晃而过——拉雷恩同样关注女性的创伤和精神世界,而在他的镜头之下,杰奎琳的内心连贯、流动、富于变化,观众可以清楚地感知到一个没有主体地位的“夫人”在肯尼迪去世之后是如何在遗孀、母亲、国母等诸多身份之间游移、挣扎,最终回到女性自我本身。相较之下,多米尼克的梦露则更像是不断受到惊吓和伤害的无助小动物。
导演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把《金发梦露》称为“《公民凯恩》和《愤怒的公牛》生下的女儿”,此话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原著中的“父亲信件”确实与著名的“玫瑰花蕾”有相似之处;其二,影片的结构多少与《公民凯恩》有相似之处。然而可怕的是,奥逊·威尔斯所设计的每个段落都能刻画出主人公凯恩的不同侧面,从而在整体上给出一个复杂迷人、因其结构性的断裂而充满神秘感的人物形象。反观《金发梦露》,观众在一个个人生片段里所能得到的无非是一个个完全相同的纸片受害者,糊了一层又一层,让人窒息的不是悲惨命运,而是单调乏味。它让我们不禁想问,如果虚构既不能提供新鲜可感的视角,也远比历史真实单薄,那么虚构的意义究竟还剩下什么?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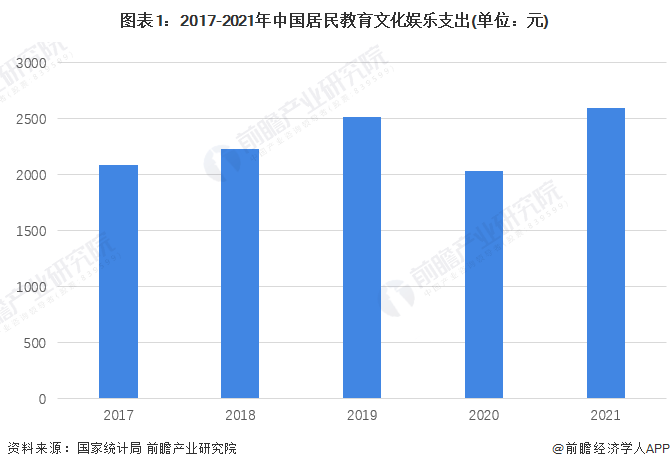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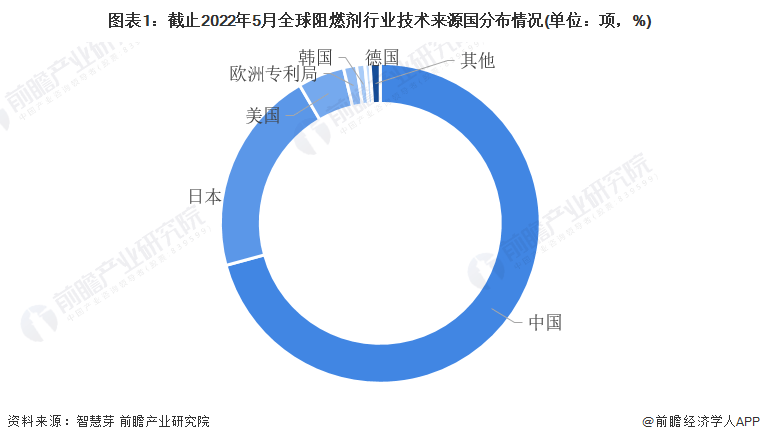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