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这是大哥给我的电报,只有4个字。
他也没说让我回去,也没说不让我回去。三年前母亲去世,我没有回去,心中留下永远的痛。我知道这一次大哥想让我自己决定。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那是40多年前,我当时在文化部剧本委员会工作,领导是大艺术家欧阳山尊先生。先生听了我叙述后说,我正在筹拍一部电影,名字叫《透过云层的霞光》。正好上海电影制片厂有点事儿,你顺道帮我办一下,这样这一趟的费用可由剧组报销。我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我坐在去上海的飞机上,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东张西望,20分钟后就闭上了眼睛,又想起了大哥的那份电报,想起了父亲。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聪明得有点过分,农民里很少有像他那样的。他只上过半年学,应该不认识多少字儿。但从我幼年起,就经常看到他读书。他戴着一副老花镜,书卷成圆筒,手伸得远远的,嘴里念念有词。他经常读的是四大名著,还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书里的故事。
母亲是他最忠实的听众,我们也很爱听他讲。讲得最多的是《水浒传》和《西游记》。灶台上经常放着几本书,除了一本黄历外,还有《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话本。这些都是父亲从邻村淘换来的,有的书连封皮都没有了,有的只剩下了大半本,但父亲都当作宝贝。
庄上有一个小广场,阳光很好,又很背风。冬天,庄上男女经常到那里聚集,男的在地上打草鞋,女人一般做点针线活。人群中间空着两个座位,一个是软的,好像是蒲草编的凳子,一个是硬的。软的是留给父亲的,硬的是留给我的。父亲怀揣着书走来,我跟在他后边。父亲在蒲凳坐下后咳嗽两声,就开始说书。他说得抑扬顿挫,遇到“有诗为证”这些有韵的地方,就唱了起来。
听的人很投入,随着父亲的演唱,一俯一仰啧啧有声,有时哈哈大笑,有时唉声叹气。说到要紧的地方,女人们还常常停下手里的活儿去抹眼泪。父亲唱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很自得。我在旁边嗓子早就痒了,直到父亲咳嗽两声说,我得抽袋烟,才把书递到我手里。我抖擞精神,也学着父亲那样边说边唱。其实那时我才上小学三四年级,好多字并不认识,但是我不去问父亲,也不打磕巴,囫囵吞枣一气呵成。听下边的人说,这孩子嗓子铜钟似的,唱得比他爸还好。
有一次连下了好多天雨,有一户人家来请我和父亲到他们家里去唱,也就相当于堂会。我和父亲穿着蓑衣走了二三里路到了他家。一看听的人很多,有的是亲戚,有的是邻居。我和父亲抖擞精神,给他们唱了一上午,听的人笑眯眯的,脸上红扑扑的,看来都很高兴。
中午的饭很丰盛,有些东西我从来没吃过。下午我和父亲又给他们加唱了一场,直到傍晚我们才又穿着蓑衣回家。
我后来对文史有兴趣,对文字也很敏感,可能跟那几年的经历有关。
上海的活儿很简单,也就是到上影厂给一个人送一个剧本,并转达欧阳先生的几句话,忙完事儿赶紧奔火车站,我要坐火车去镇江。
我到镇江时已经很晚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北的轮渡都走了,轮渡码头已经锁门了。我跟别人打听,明天早上最早一班船是五点,没有办法,我只得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那家旅馆真小,一大间房里住了很多人,大约有几十个都是上下铺。老板说只剩下靠门口的一个上铺,我也管不了许多,赶紧爬了上去,请老板明天早上四点钟叫我。
躺在床上也没脱衣服,脑子乱乱的,我知道也睡不着。
我又想起了父亲。父亲外号叫火星子,那意思是说脾气火爆,一点就着。这外号有褒有贬,褒是说他刚正不阿,爱打抱不平,哪有不平的事情,他就要去踩上两脚,把它踩平。贬是说他认死理儿,一根儿筋。母亲说他年轻时方圆几里内如有家庭纠纷,经常有人请他去评理,因为他说话公正又有威信。
我亲身经历过两件事,倒也有趣。有一次父亲上街赶集,我那时大约七八岁,也闹着非要跟他去。我们刚走到村口就发现有三个穿军装的人在那里割几棵新栽的小树。父亲上去对他们说,这是新栽的树,你们怎么能割?那几个当兵的转过脸来说,你是什么人?父亲说,我是老百姓来赶集的。那人说这是你家的吗?父亲说不是,但不管谁家的,这新栽的小树也不能砍了。那些人说,你找揍是不是?其中有一个人说揍他,另一个说带他回去到屋里吊起来打。然后他们三个人就夹着父亲往庄上走,我跟在后边两腿发抖。
父亲被他们带到一个院子里,那家院子的主人和父亲很熟,问明了缘由以后,求几个当兵的放了父亲。父亲还继续去赶集,我还继续跟在他后边。中午回来的时候,父亲看见庄前的河边,有一个解放军模样的人坐在那儿钓鱼,父亲想那一定是个大官,父亲上前把上午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后来听说,当天下午那三个当兵的就被关了禁闭,又听说那几个人原来是国民党兵,对老百姓横惯了,刚刚俘虏过来不久。
别看父亲性格暴躁,但是他挺有善名。父亲年轻的时候得到一个治破伤风的秘方,那时农村医疗条件不好,破伤风就能死人,父亲救活过好几个人。有一次,一个女人在河里割柴火,得了破伤风,怎么也治不好,快要死了。他们找到了父亲,父亲去把她救活了,那家人要给父亲钱,父亲不要,给父亲粮食,父亲也不要。父亲回来说,那家有好几个孩子,还有老人,都快揭不开锅了,我怎么能要他们的东西?村里有一个叔叔,父亲把秘方也告诉了他,后来叔叔经常外出给人家治破伤风,收钱也收粮食。这话传到父亲耳朵里,父亲笑笑说,能治好了就是好事。
第二天早上,我乘头班船过了江,又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路过家乡的汽车票。路很远,汽车要走六七个小时,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几里地。我坐在汽车最后一排,有点冷。汽车要经过美丽的洪泽湖,我是很想好好看看的,但是不一会儿我就迷糊了。
我们家有三个兄弟,我是老二,也最调皮,常常受父亲的打骂。父亲老年的时候,我曾经开玩笑地跟他提起过这事。父亲一脸冤枉,说我从来没打过你。其实父亲什么时候打我,为什么事儿打我,打在哪儿疼不疼,我记得可清楚了。但是看着父亲的一脸无辜,我知道他都忘记了。父亲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些打骂,在我心里都是最温暖的记忆,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到家里已经很晚了,我跪在父亲的头前,他很安详,像是在睡觉。以前我经常看他睡觉,他都是这样安静。
送完父亲,我们走在村外的一条土路上,我记得那条路是父亲经常走的,他在这里80多年,这条路上肯定布满了他的脚印,我走得很慢。我想我是在踩父亲的脚印,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点温暖。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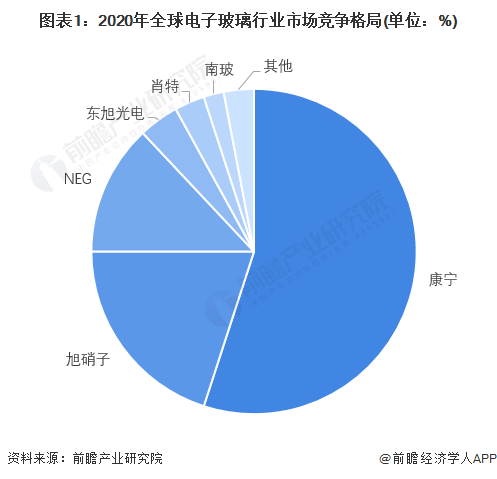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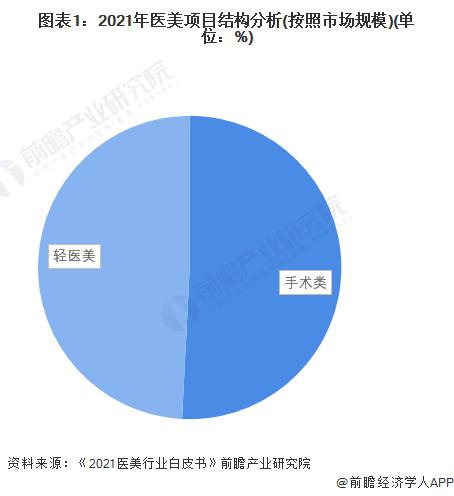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