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著名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1945年生,1972年至1978年曾任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先后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哈佛大学,师从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创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
 【资料图】
【资料图】
《豹迹》 巫鸿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巫鸿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证。
与以往的学术著作不同,对于巫鸿来说,新作《豹迹》是本特别的作品。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一个人的生活含有和影子一般多的瞬间经验,它们随时发生和消失,永远属于当下,因此没有时间性。它们仅属于自身存在的时刻,只与此时此地的身体和环境相关。”
在巫鸿看来,人生本不存在百分百还原的回忆,任何回忆都是对往昔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必然牵扯当下,形成投射于当下的影子。因此,本书绝不是一本“标准”的回忆录,而是“记忆写作”,也就是以“现下的我呼唤过去的我”。由此而生发出色彩斑斓的叙事、形象和线条,构成了本书清新、流畅的韵律。
巫鸿的父亲巫宝三是江苏句容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母亲孙家琇是浙江余姚人,1939年获美国蒙特霍留克大学研究院戏剧文学系硕士学位。巫宝三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认识了正在该校学习剧本创作的孙家琇,后来,巫宝三去柏林继续求学,孙家琇从美国赶来,他们结婚了,并一道回国。
巫鸿1945年出生于四川乐山。长他几岁的姐姐,出生在云南昆明——那时,他们的父母刚刚回国不久,父亲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母亲在西南联大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巫宝三一直任职于社科院经济所,而孙家琇则在中央戏剧学院任戏剧文学系主任、教授。
巫鸿的童年、少年,乃至大部分青年时期,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戏称自己是“在后海边上长大的孩子”。他在海淀区宝福寺小学读小学,在北京101中学读初中。101中学是一所建在西郊圆明园旧址上的学校,新中国成立时从解放区迁徙至此。1963年,巫鸿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年至1978年,在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工作。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
关于北京的记忆,巫鸿写在《发现北京:场地的记忆》这篇里。但在此篇开篇,他便表现出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忧虑。这与他后来的求学经历有关。1980年至1987年,他像曾经的父亲与母亲一样,远赴哈佛大学,在荣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之后,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留校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
别家离国的几十年,让巫鸿产生了记忆危机。祖国变化,日新月异,他担心北京那些“保存记忆的场地正从地表上消失”,他该如何在记忆文体里完成历史与个人叙事的双重呈现呢?
然而,检索记忆深处,那些与血肉粘连一处的记忆,不请自来地从巫鸿笔下喷薄而出。他以轻松的笔触写下:出了胡同就是后海,隔岸能远远地望见钟鼓楼。过了银锭桥就是烟袋斜街,走到钟楼与鼓楼之间的空地,有不少人在摆地摊,“药材、古玩、书籍、盆花、金鱼摆了一地。周围还有耍猴的、练把式的、算命的、拟写书信的,每个摊子前都聚着一堆人,引起我的好奇心”。
诸如此类的记忆影子,从来未曾离巫鸿远去。幻影流动之间,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巫鸿甚至还忆起,“第一次去天安门,我还是小学一二年级,一个星期天父母亲带我和姐姐去紫禁城参观,就是原来的皇宫”。巫鸿的散文,的确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魅力,读者并不觉得他的文字遥远,反而在脑海里瞬间汇集成了一幅图景。
故土难离。巫鸿关于故人的记忆是由保姆李妈开启的。李妈是旗人,与北京有着紧密的联系。巫鸿能够迅速地刻画出李妈的身材、面貌,行为习惯,甚至连她那一点点对日常生活认知的谬误,也能及时地捕捉到位。李妈与旧时的一千元纸币一样,渐渐地走出了我们的记忆,任谁也挽救不回来,但那些值得记忆的人与事,永远也忘不掉。
巫鸿年逾古稀,身为学术领袖,交游广泛,但在本书中,巫鸿想写的人并不多。除了李妈,还有忘年交丁声树、朱丹、俞伟超和费慰梅,再有就是同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的学长杨新等。可惜,杨新已故,享年60岁。
尤为被巫鸿浓墨重彩书写的,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导师张光直先生。书中有张半身黑白照,摄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张先生,强壮、儒雅,双眼闪着真诚的光芒。隔页有张巫鸿在哈佛大学湖边拍的彩色照片,他身穿中式对襟上衣,满脸笑容,阳光帅气。这样的两个人,亦师亦友,共同徜徉在学术的海洋里。与其说他们是在传承学术衣钵,不如说他们在灵魂的气场中相互吸引,芳香飘溢。
乌镇的木心,在巫鸿心里也有一个独特的位置。这一点,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看得出来。巫鸿在写完关于敦煌考古随想的《豹迹》之后,紧跟了一篇《木心在哈佛》。要知道,木心并非专业学者。他是画家、作家、诗人,总之是个散淡的人。与巫鸿相识时,木心57岁,巫鸿差不多40岁。木心是先到纽约的前辈,巫鸿是通过陈丹青认识了他。两人一见面,便视彼此为知己。木心成了《豹迹》的第一个读者。在结尾处,巫鸿写了一只断爪的雪豹,勇敢而孤独。木心是否在敦煌斑驳的遗迹里,在雪地上拖着残肢而行的豹子身上,看见了自己,未可知。但他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了《联合报》的主编痖弦。刊登出来之后,巫鸿说,他写的是“幻想性的回忆”。
本书结尾,巫鸿再写木心,再次呼唤那只孤独残缺的豹子。他说木心是隐士。想起木心的诗:“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在巫鸿的朋友中,一定是最难琢磨的那一个。但是他们相互懂得,始终用记忆勾勒对方的影子,真是难能可贵的人生记忆。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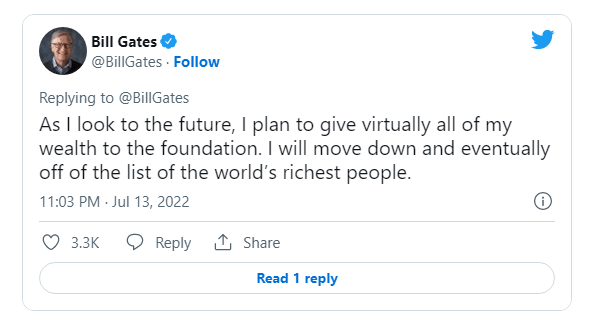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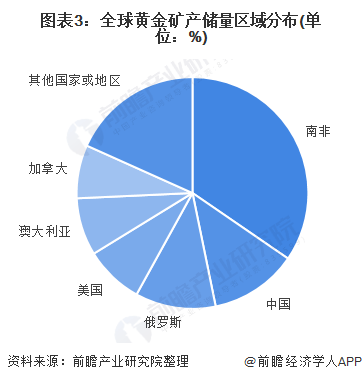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