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以任鸣对戏剧的赤诚之言——“戏剧就是回故乡”为题,一场围绕他和他的戏剧艺术的追思与回顾,以“任鸣导演艺术研讨会”的方式,在他身后举办。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次研讨会由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戏剧家协会、《新剧本》杂志承办。作为导演、作为北京人艺的掌门人,任鸣接续传统、创新表达、培养新人,他一生有近百部导演作品,却低调到生前从未有过一场围绕他个人导演艺术的研讨。关注他的评论家、学者,与他共事几十年的同事、同行,感慨他是“被严重低估的导演”。
任鸣院长的离开很突然,对于北京人艺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损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入职的时候,北京人艺正好到了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老艺术家已经开始离去,年轻的一代又没有起来。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茶馆》谢幕演出的时候,台上、台下、后台都非常热闹,没有参加演出的人也要看一看这个谢幕演出,台上的演员也下不去,都像在这样一个时刻做最后的告别似的。我站在上场口看谢幕,没有控制地哭了出来,当时就觉得怎么办,天塌了。那个时候任鸣也很年轻,他后来当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用相当长的时间为北京人艺的今天打基础。
任鸣很幸运,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北京人艺,能够在曹禺先生、于是之老师、林连昆老师、朱旭老师等等前辈的呵护下成长,在还是四级导演的时候,就破格进入人艺艺委会,这是当年老艺术家对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培养。
任鸣一生尽管很短暂,但是很辉煌。任鸣导演说自己一生只干一件事,就是做导演,做人艺的导演。他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在这个单位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就是导戏。他一生导演了90多部话剧,在人艺创作的话剧有50多部。现在我在帮助恢复他的《油漆未干》,他还有大量的古装戏、京味戏、现代戏、外国戏,未来任鸣导演作品的演出,还需要年轻导演承担起来。
北京人艺是一个具有探索精神和开放性的剧院,可能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艺特别传统,作为一个有70年历史的剧院,有很多老传统、老规矩,但纵观北京人艺的历史,是相当有创新精神的。
首先在焦菊隐先生、曹禺先生的带领下,开创了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开创了话剧民族化的道路,而且到今天这一表演风格在全国独树一帜。
还有,中国的小剧场话剧、早期探索性的戏剧,都诞生在北京人艺的舞台。当时剧院能够放手让林兆华老师去做,也说明了北京人艺的探索精神。
在任鸣导演50岁左右成为院长后,无论作为院领导还是导演,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北京人艺擅长演京味戏,其实人艺的京味戏并没有那么多,正是因为独特的表演风格,让大家认为北京人艺最擅长京味戏。任鸣从导演《北京大爷》,就跟林连昆老师在京味戏的形式上有一些探索,到《北街南院》《全家福》,到近些年的《玩家》,在表演、演出形式、舞美形式上开启了新京味戏的探索。我们剧院有一句话叫“一戏一格”,他一直在践行,他导演的每一部戏都是任鸣的,但都有新意。
任鸣导演了《知己》《我们的荆轲》等古装戏。他曾经跟我聊,提出了“新东方美学”。话剧民族化到底怎样借鉴戏曲?早期的《虎符》用京剧的锣鼓点,到了《蔡文姬》,没有京剧的锣鼓点,但演员还是按照戏曲的步态行动。今年徐帆再次演出《蔡文姬》,完全是利用了她学过戏曲的优势,在舞台上按照京剧程式化的方式去表演。任鸣从《知己》开始在新东方美学的概念下探索,已经弱化了很多纯戏曲的动作,在形式上有戏曲美学的感觉,但是又探索了一种新的表演方式,生活化一些。
任鸣这些里程碑式的探索,不一定引起轰动的效应,但是对人艺的发展确实有引领和思辨的作用。
人艺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有独特的一批人。我们的外国戏也是这样。我们幸亏有英若诚先生,英先生在把《哗变》引入中国的时候,曾被质疑这个戏是否能在中国有生命力。原因是它是男人戏,没有一个女人,演员上来就是坐在那儿说。英若诚老师说,上了台你们就知道这个话剧的魅力。当时任鸣是这个戏的副导演。有很多关于这个戏的传说,比如导演赫斯顿掐着秒表让演员读台词,因为他听不懂中文,但他要求语言节奏,必须保持这个节奏把台词说完。这也开启了中国演员对表演的另一种认知——还可以这样要求我们去完成表演。朱旭老师当时跟我们聊,他在演《哗变》的时候才明白,我们认为的一些剧场效果,赫斯顿认为是不需要的,如果单纯为了笑声和掌声而演,对这个戏是有损失的。
后来我再接着演魁格,也意识到大段的台词和交锋不应该单纯地顾及观众的反应而演。这也是于是之老师的看法,我跟任鸣探讨过于是之老师的表演,他不会因为观众在这里笑了,明天我就在这里夸张一点,后天再夸张一点,他永远在保持人物的“度”,不是为了博取笑声和剧场效果。
英若诚老师留给我们外国戏中国化的翻译。《哗变》翻译出来演到现在没有改过一句话,也没有一句中国人认知的外国戏应该那样说的台词,英先生的翻译寻找的是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任鸣导演有传承精神,北京人艺历史上留下来的优秀传统,他绝对要坚持,他一辈子都在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风格。通俗的理解,现实主义就是生活化,但其实不然。现实主义可以是荒诞的,可以是超现实的,但是一定跟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荒诞戏在中国没有沃土,如何改变,是文艺工作者的问题,不能强加于观众,责怪观众看不懂。
任鸣导演还留下很多自己的创作感受和体会,完成了《导演的思想》《戏剧的力量》《舞台的魅力》等著作。
杨乾武老师那天在追思会上说了一句话特别好:他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导演。他也是一个值得被研究的导演。
任鸣导演离开我们了,但我又觉得他并没有离开,大幕开启的那一瞬间,他就在。他秉承着承上启下的责任,培养了徐昂、闫锐、唐烨、韩清、杨佳音等导演。我做导演,也是他跟我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你应该做导演,你一定要去做导演。我在他的鼓励下也开始自己导演方面的发展。
当今的中国戏剧已经不是非要讲中国化的问题,中国化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化了,只是化到什么程度,怎么化,如何传递东方文化。我相信北京人艺会传承这些精神,任鸣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财富,请相信北京人艺不会让大家失望。
任鸣的去世时间写的是19点29分,那天,还有1分钟,人艺的大幕就拉开了。上个月《哗变》这轮演出的最后一场,开幕的时间是19点29分,致敬我们的院长任鸣先生。
本文据冯远征在“任鸣导演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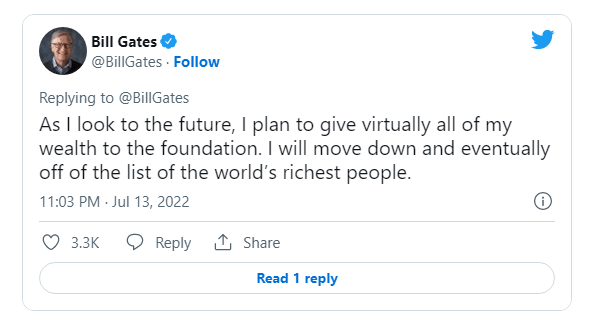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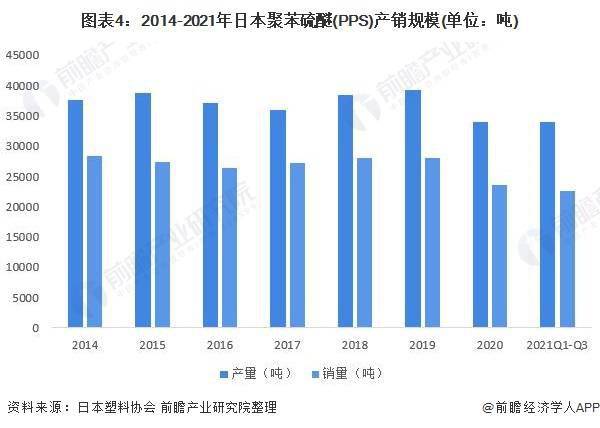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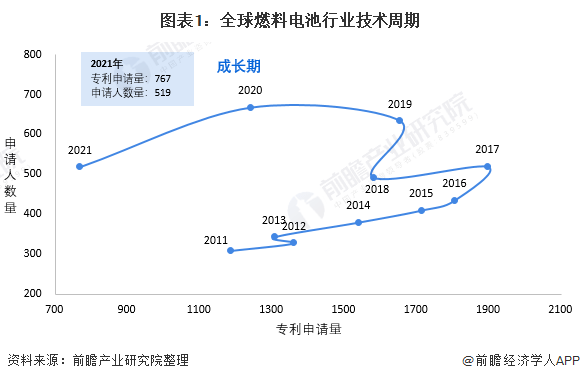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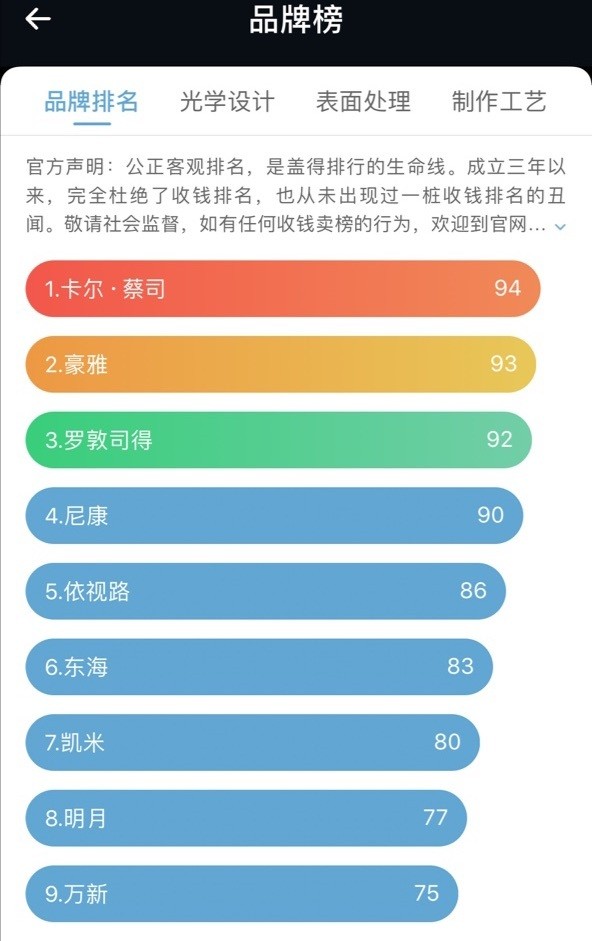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