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第一次看杨葵写字,是在一个饭局上。对能写一手好字的人一向刮目相看,更钦佩即席挥毫的自信和诚恳。那次杨葵写的是隶书,后来,他给自己散文小集《东榔头》《西棒槌》的封面题签,又换成小楷,一丝不苟。及至2016年“杨葵书法展”,才发现,篆隶楷行草,他多有研习,且自成一体——他的“楷”里,偶见“行”的峻急,他的“隶”中,也多“篆”的圆劲。“纸边儿”书展上,我特喜欢他“想见古人”“心如朗月”一楷一隶那两幅小轴,那8个字合在一起,就像在说他的人、他的文。
也许,对杨葵而言,文如其人外,也是文如其字。翻阅他的散文随笔,篆隶般的醇厚、唐楷式的淡定随处可见,不同是,很古之外,他的文字也有很新的一面,翻阅新近出版的杨葵自选集,这种印象更为确切。“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三册书名出自陶潜诗句,这种借五柳先生遣兴抒怀的选择古意盎然,可那三册自选集的封面配图、书名用字,却新意盎然:书名字选康熙字典宋,矜持古雅,封面图选画家范薇彩墨小品,清澈明媚,这种亦旧亦新的组合浑然天成,老话说,“如将不尽,与古为新”,讲的大概就是这种吧。
为考证《寒柳堂集》中一联诗句的真伪,杨葵翻阅了1980、1982两年三个版本的“陈寅恪”,他发现,80初版《寒柳堂集》之《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中,腹联两句中的那个虚缺号,既非编者所谓“脱字”,亦非被胡乱充填后的“完整”,而是心魔作祟的搪塞、支吾或苟且。由此,杨葵慨叹,“书籍是由人一笔一画创造出来的,但书籍最大的敌人,正是人自己。”在《静寄东轩》一辑里,类似的杨文很冷:一丝不苟,郑重其事。
而在《愿言怀人》一辑,杨文又自冷而暖,温厚敞亮。在杨葵眼里,所谓朋友,情同手足,亦师亦友。从翻译家盛宁的译文里,他领会信、达、雅;从昆德拉的《不朽》里,他参悟道路、公路、意义;从理发师小张滴溜乱转的眼神里,他感受因缘、闪失、奔突;从王安忆信笺的字迹里,他揣测忐忑、笃定、淡然;从语文课代表小连“白轮船”的秘密里,他体验相遇、分离、猝不及防……杨葵文字的亲切与冷峭参互成文,合而见义,让人想起汪曾祺笔下憧憬温煦甘醇之境的那8个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最终,让人超越“冷”“热”偏见的,是《枝条载荣》中“苏北笔记”“北师大轶事”两组札记——苏北童年回忆、师大青春回忆这两组往事的交织,让或冷或热的叙事调性有了冬寒抱冰、夏热握火那样一种飞跃。2016年,杨葵回苏北老家,旧地仍在,沧海桑田,临了,他从一幢旧楼顶俯瞰故里,“突然昔日重现——树!那些树!人事来了又去,建筑千变万化,但是那些老树,从未变过方位。借着那些曾如此熟悉的树,我逐渐清晰辨出当年的离家上学之路,再以这条路为参照,一一辨清当年家在哪里,操场在哪里,食堂在哪里……”
这个位居“俯瞰”维度的杨葵敏锐、深情外,还多出一种同龄人身上不常见的怅惘。自选集里,杨葵说,时间、生物、语言等维度外,最最无法割舍的“乡愁”,即何炳棣先生所谓“籍贯观念”,只是其影响“更隐晦,更深入,不易觉察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别老以为自己是多么先进的现代人,千丝万缕的旧礼教、旧文化的影响,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很多,没那么容易摆脱……”而这种建立在自省、自觉基础上的文化乡愁,刚好特别杨葵——是簇新的古旧,也是新锐的老到,一如他日益精进的法书,“至简至拙,却从心底流出”。
二零二二年八月五日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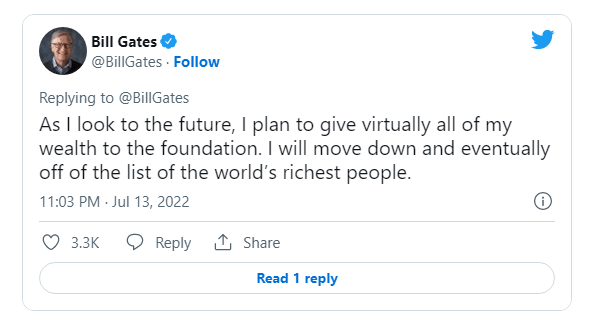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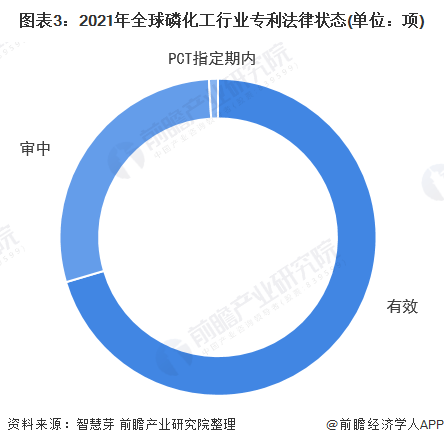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