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择明
展览:坚净——纪念启功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特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展期:2022.7.22-8.5
地点:嘉德艺术中心
或许因为工作关系,竟也一直有好奇者问我“启功的书法到底怎么样”,我只一律答“好”,或“不懂”。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事情。今年是启功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嘉德艺术中心举办了“坚净——纪念启功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特展”,和同时在同一地点举办的其他几个展相比,可以说非常低调了。但是一想,这也正是启功先生一贯的风格,而且这也是讨论一下启功书法的正当理由——特别是涉及关于“传统文化”当下的某些问题。
启功的字
不过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有些年头了。我读中学的时候,似乎有一段时间社会上有过一阵“硬笔书法热”。某天从邮局买到一本《中国钢笔书法》,刊名题字也是钢笔字,但感觉跟平时看到的“名家”风格大不一样,落款便是启功先生。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很有些古文造诣的,他端详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很满意地说:“老一辈有学问的人,就是这么写字的……”
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教我们文艺理论的刘宁先生就住在启功先生楼下,遂得以接近传说中的“小红楼”。但它其实并非什么豪宅,只是比其他教工住宅宽敞一些,四周清净一些罢了。我们同宿舍恰好有一“古籍所”的研究生,在听到我表达对见到“书法家启功”的兴奋时,不禁“嗤”了一声,好像笑话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他的大意是,启先生是鉴定家、古典文献学家,古文专家,人家从来没当自己是“书法家”,字写得好,是文化人的本分云云。
应当说在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启发,但认同“文化第一性”的同时,有几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就是书写、书法、艺术、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启功先生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是“书法家”,那么他自己到底怎么想的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我们提及书法家启功时,我们是否又能进入书法内部去看,而非他的名头、牌匾题词、甚至电脑里的“启功体”去看呢?
启功先生可能是“前现代”意义上最后一个书法大师。“前现代”不是线性意义上的历史时间,比如,今天的艺术家也完全可以成为文艺复兴式的人物。那么,在“前现代”意义上,书法首先与“写字”相关,它既指书写的视觉,也指书写的内容。
在表意文字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不是中国书法所谓的“书法”,尽管很多古老语言文字都极为讲究外形(线条)的视觉美,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书写的神圣性的认同。知识就是权力——书写,就是通往权力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书法家,大都是官员,另一部分是不屑于做官的“名士”——但他们首先有不走仕途的资本。王羲之、宋四家、赵孟頫,哪一个不是高官呢?书写,包括了文章(思想文字)和呈现文章的方式,这两者是不可分的,文章里没有学问、思想、见地,是当不了官的;字写得不好,也是当不了官的,这两者之间是一体的、互为表里的。这就是为什么科举时代如果字写得“不好看”就没法在文人士大夫社交圈混的原因。这里的“好看”,首先是指视觉上的“秩序感”,只有在“秩序”建立的基础上,才有发挥“艺术个性”的余地,法度森严的唐楷如此,“尚意”的宋人亦如此,不信你看“米癫”的《向太后挽词》,那一个规矩,哪里敢有半点儿“癫”的样子?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儒家经典文字中心主义”,或许说明了为什么到了后来“馆阁体”会成为主流,尤其是明朝的沈度之后。这个是事实——书法的“传统”中首先是书写性,而书写又来自四书五经等“学问”。首先把字写好看,写工整,是读书人的基本要求,如此而已。
启功先生虽然年幼丧父,但作为王室嫡亲,他确实受到了那个时代可能的、最好的传统教育,这对他艺术风格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面有皇家的教育,包括溥心畬、溥雪斋这样的文化素养深厚的大艺术家、皇室宗亲,也有像陈垣这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的大学问家。但在书画方面他还是延续了皇家的传统——这一点本身无可挑剔,只有在皇宫里才能见到最好的中国书画是什么样的,以及能够在最初的、很年幼的阶段就能掌握核心的用笔方法,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奢侈的。
皇家的传统意味着与民间的风格有很大区别。实际上当时社会上书法的风气是康有为发动的“碑学”,但他矫枉过正了,向民间学习没错,但学习的应该是那鲜活有生命力的一部分,而康有为提倡的学习对象却有很多“粗头乱服”,误导了很多学书法的人,不过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种面向民间也在事实上拓展了书法的视野。这里的关键在于,启功先生无悬念地延续上了最传统的那一部分“帖学”。曾有人批评启功先生一笔“馆阁体”,他笑应“我哪里有馆阁体写得好”,这里启功先生并非为了谦虚而谦虚,馆阁体要写好,非得下大功夫不可。首先是书写内容,即文字本身不能出错,用今天的话说,“古文功底”绝对要经得起挑剔;其次用笔、对文字结构的掌握要几乎无可挑剔。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有的意见认为启功先生“不会悬腕”“写不了大字”“点画细瘦放大了不好看”,这些都是误解,只要看看展览中的几幅大字就可以知道,“腕不论低与高”,启功先生的笔力,绝非一般书家可比,比如“骖鸾”二字,杂有飞白之意,如“骖鸾跨鹤”,气势撼人。
启功的心
当然仅仅写得整饬,毫无破绽,对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在古人那些仿佛无意之作中,尤其是手札中发现了更理想的中国书法史,在晋人的“萧散”中发现了某种艺术的真谛。需要注意的或许是,魏晋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是一种氏族门阀制度的、“贵族之家”的社会,并非“大帝国”,这有利于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个性。这种特殊性也使“魏晋风度”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一种向往。文人士大夫有很多精神呼吸的方法、心灵的出口,琴棋诗书画都是手段,在这些实践中,他们往往取道家、佛家的精神路径,“独与天地相往来”。
清朝的贵族同样不例外,启功先生九世祖雍正皇帝还打扮成“隐士”的样子,留下各种“行乐图”。但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的,因为它要求很高的文化水平。就像《红楼梦》里描写的那样,贵族子弟社交雅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作诗。整个清代的贵族对唐诗烂熟于心者多矣。诗写得好不好,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里的诗,不同于现代诗,除了要合乎韵律,有新意,还要调动相当的知识储备,那就需要相当扎实的“古典学”储备,而且又不能故作艰深。我们在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里能感受到唐诗的那种美学取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另外一个重要的“心灵出口”对于启功先生来说是佛法。他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雍和宫得到了高僧灌顶,并终生保持了对佛法的闻思修,而且他谈到自己的信仰时总是非常坦然。我们在很多寺庙或许目睹过启功先生的墨宝,这是他的“供养”。至于平时和佛经相关的书写更是不计其数,他也坦然落款“优婆塞启功”。优婆塞,就是居士的意思。这次展览中有多幅精彩的相关作品,佛法浸润到他的生活之中。在展品里有一件王雪涛画的蛤蟆,又有陈佩秋所绘《双蛙图》,这些都跟启功对“蛙”的喜好有关,他有“蛤蟆禅”印一方,常钤印在作品上,因为“蛤蟆无更多本领,只此一跳”。看似谦虚之词,实则暗藏禅意。据启功先生本人说,学佛给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慈悲为怀”。这一点其实必须在佛法中才能得到解释。慈悲,不是大众语境中的那个意思。慈,是“予爱”,意思是“把我的爱献给你”;悲,是“拔苦”,指的是将众生从轮回苦海中拯救出来。慈悲,不是盲目的“可怜”,它必须和智慧结合,即“智悲双运”。先生“宽以待人”,或者被人理解为“没有原则”,实际上需要从佛法的见地上出发。这种见地或许也解释了先生的字很少有强烈的情绪波动,即便是他在临那些以情绪大起大落著称的作品时亦如此——都化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宁静。学佛,首要任务就是“调伏其心”。这从艺术就是张扬个性的立场来看显然会觉得启功的字索然无味的原因。但正如宋人邵雍在诗中写到的那样:
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点是,启功先生对传统的承继是不具有复制性的。他本人对传统的学习是别人学不了的。早已不再是“写字”的那个时代,比如,我们今天没有理由要求中文系教授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没有理由要求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写一篇像样的古文——书写早就失去了“道统”的功能,现代的分工转型早已经转向了“书法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要有怎样的“全人类的”视野,怎样有选择地从“传统”中汲取养分,是更为现实的任务。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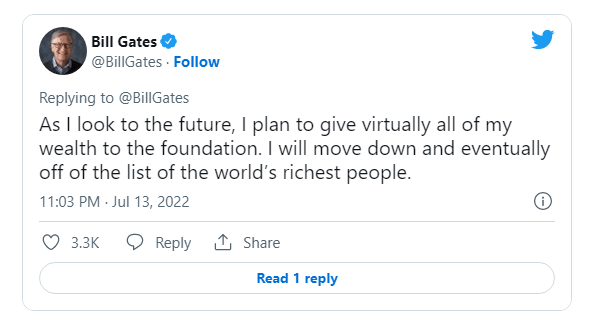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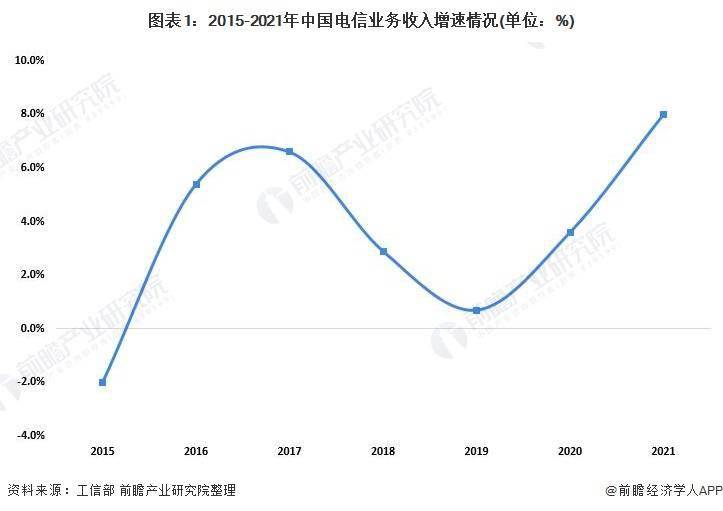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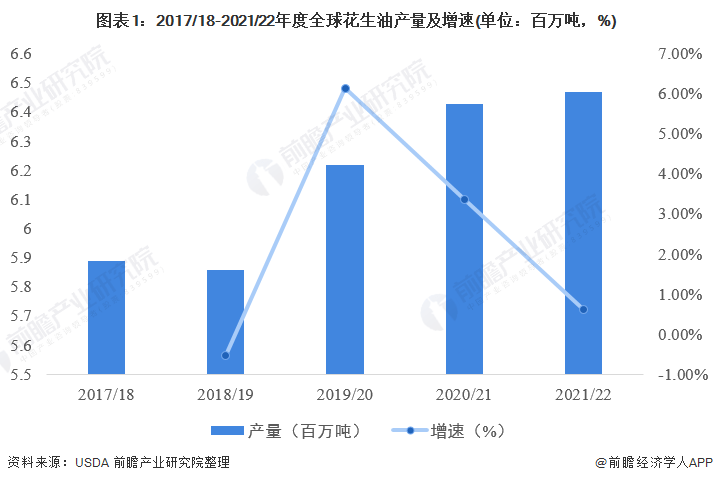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