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5日,著名导演林兆华在北京人艺三楼的排练室里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绝对信号》,由此拉开了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帷幕。40年来,小剧场戏剧以探索试验的姿态,为传统戏剧观念带来冲击,为舞台形式输入新鲜血液。
20年后,国内第一个民营小剧场——北兵马司剧场(圈内人称北剧场)正火的时候,戏剧导演曹曦正在中戏上大二,那是他除学校外去得最多的地方。在那里,他看孟京辉的《恋爱的犀牛》、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连轴转地看国内外形形色色的戏剧展演。据他回忆,等候入场的观众有时能从北兵马司胡同一直排到交道口的大街上去。彼时的北剧场,不仅是年轻艺术家们肆意挥洒艺术想象力的平台、海内外戏剧市场的一座桥梁,也是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坐标。
而这个承载着太多人激情、梦想和回忆的平台,就是由一个叫袁鸿的瘦小四川青年和他的搭档水晶构筑而成。
 (资料图)
(资料图)
1.写剧评帮人多卖几张票
袁鸿,上世纪70年代生人,最初被戏剧触动心弦是缘于从黑白电视机上看到电影版《茶馆》。与上世纪90年代诸多文艺北漂一样,初到北京的袁鸿,一头扎进热闹非凡、生机四溢的京城文艺生活中,拼命汲取艺术养分。小剧场戏剧的原创性、野生性、颠覆性,让他对这一艺术形式情有独钟,不知不觉,从一个小剧场戏剧爱好者、剧评人到参与其中帮忙做事情,到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袁鸿长达几年义务劳作,尽自己所能宣传推广他所喜爱的小剧场戏剧。很多时候,看完一部令他激动的戏后,就坐在剧场旁边的咖啡馆里奋笔疾书,为报纸写着没有稿费的剧评,他的心思特别简单,就是希望“这么好的戏,多一点人来看,多帮他们卖几张票”。
2000年,年仅27岁的袁鸿以制作人身份推出的话剧《切·格瓦拉》在人艺小剧场连演47场。每次演出结束,都有七八成的观众不愿意立马走,而是会留下来参加演后谈。交流的气氛热烈而真诚,每个人都很认真,有的时候会变成现场辩论大会。剧场关门,大家便在剧场外边的门口聊、院子里聊、马路牙子边聊。
人艺旁边的胡同有个小饭馆,最后留下不走的人经常会一起涌到那里,一人点一盘廉价的饭菜,认识的、不认识的拼上两三桌,把小饭馆变成艺术沙龙,坐在那里继续辩论。其中有很多学者、经济学家、文艺工作者,各路大神的精彩言论让饭馆的老板大受感染,后来索性将饭馆改名为“剧人之家”。“他们家的炒饼和熘肝尖非常好吃,我现在都很怀念。”袁鸿如是说。
2.第一家民营小剧场
那时的北京,还没有一家民营的小剧场。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剧场,将国外优秀剧目请进来,成了袁鸿越来越强烈的心愿,而更直接的动因则是彼时正在野蛮生长的大学生戏剧。
从1982年《绝对信号》开始,历经十几年的孕育,到上世纪90年代,戏剧这个小众的艺术形式已经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所迷恋,尤其在大学生中,原创戏剧作品多如牛毛。
2000年左右,是北京高校剧社团体特别活跃的时候,用袁鸿的话说,“有新千禧的懵懂在”。那几年袁鸿密集地看各大学的戏剧,也帮他们做校际交流。大学生戏剧虽然青涩粗糙,但袁鸿却从中感受到一股新鲜的力量。当时的人民大学八百人大教室,每年五四青年节都会有一个戏剧小品比赛。由于组织经费有限,初赛、复赛、决赛,会在一整天内一气呵成。袁鸿从早上8点就去,一直看到深夜,期间屡屡被打动。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个关于海子的小戏叫“春暖花开”,没有复杂的舞美和调度,台词就是散文诗,一句一句朗读出来,那些朴素又坦诚的诗句带来的巨大的爱的力量潮水般将观众吞没。
他还记得,《我弱智,我无罪》的女演员由于没有演出经验,重重地跪在舞台台阶上,膝盖磕破了,血溅到白色的裙子上,她都毫无知觉,只是奋力地要把戏演好。大幕将落,整个八百人大教室静极了,十几秒后,炸裂般的掌声传出,大家不停地哭——时隔20年,袁鸿依然能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曾经令他激动万分的现场。
这些青涩却又充满真挚激情的大学生戏剧,让袁鸿产生了一股莫大的责任感,他要把那些学生戏剧带到校园以外更广阔的地方。这件事并不容易,所幸这个单纯而勇敢的愿望得到了诸如人艺小剧场的傅维伯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所的田本相、宋宝珍等学者的支持,他们纷纷用自己的身份去与北京戏剧家协会沟通协调,最终促成了大学生戏剧节的举办。袁鸿把自己攒的近2万块钱全部拿出来投入其中,而人艺小剧场则收了很低的租金来支持学生们。
2001年,第一届大学生戏剧节一炮打响;2003年,当袁鸿拥有了自己的剧场,他把第三届大学生戏剧节邀请至北兵马司剧场举办,同时也将舞台扩展到了更多剧场。半个月,25场戏剧演出,纯公益性质,全部免费。大戏节成为学生们的文艺狂欢节,同时也让北剧场成为文艺青年们的心灵归属地。2004年,为了控制人流,改为收费制,但针对学生只象征性收费5元。至此,大学生戏剧节与北剧场的名字紧紧连在了一起。
彼时的北剧场,不仅有票价低廉的好演出,还和一些文化机构如英国文化协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等合作了许多工作坊讲座。此外一些驻地艺术家的工作室,如香港曾文通的舞美工作坊、金士杰的表演课,日常会有双周的戏剧讲座、放映观摩,一些导演、资深演员应邀参与,有的持续一周,有的仅一个下午。零距离与大师们面对面,而且活动大多免费,想想都美。袁鸿做这些吃力不赚钱的事,不过是为了把好东西分享给更多人,让他们和自己一样,从艺术中感受美与力量。
多年以后,有位已成社会中坚的中年人从播客节目《跑题大会》中听到袁鸿的声音,激动地从外地跑到袁鸿的上海工作室,请他喝了三天四顿酒。他说,他来是为了补偿当年逃过的票钱。当年还是一名学生的他,为了看懂刘深编剧的独角戏《我爱抬杠》,用一张票根连看了四场。彼时的商业演出,票价通常为150元左右,为了让更多在校学生能进到剧场,特设了40元的学生票,即便这样,依然有学生捉襟见肘。很多时候,袁鸿明明知道好多学生在混票蹭票,但也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他们那么诚恳”。为了避免规则与人情冲突的尴尬,他甚至让高校剧社的大学生志愿者检票。比起赚钱,他更在乎喜欢戏剧的人能不能看见戏剧。
但作为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钱,始终是卡着袁鸿脖子的一道绳索。2003年,刚刚开张的北剧场就遭遇长达几个月的“非典”重创。让袁鸿咬牙撑下来的是北剧场忠粉们的鼓励与实际支持。袁鸿犹记得,当时有一位工人大哥,从首钢骑车到北剧场,拿出自己的800块钱交给袁鸿,就是为了让他们保住这块场地——那只是一位普通观众,与北剧场的经营者并无私交——万分艰难的时刻,是这些质朴的感动支撑着袁鸿和他的朋友们。
优质的演出,低廉的票价,让北剧场热闹非凡,但也越来越入不敷出。当理想遭遇现实,再多的情怀也抵不过难以为继。几经挣扎,2005年,袁鸿和他的团队忍痛关闭了北剧场。一同关掉的,还有那些给予一代文艺青年巨大精神滋养的各种工作坊。这成为袁鸿心头一道不能触碰的伤。
3.“爱丁堡前沿”链接中国和世界
北剧场关门之后,袁鸿并没有离开让他快乐并伤痛的戏剧,休整疗伤半年之后,他与台湾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导演合作了《暗恋桃花源》《如影随行》《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参与了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聂小倩与宁采臣》《情话紫钗》等剧目,以及教育公益项目,其中“茶园助学”延续至今。
之后他开始游走于我国港台地区,还有日本、英国等戏剧繁盛的地方,去完成他做了很久的戏剧饕餮大梦。在爱丁堡,随处可见的戏剧场地,目不暇接的戏剧样式,让他眼界大开。他贪婪地观看戏剧,从早到晚,从海边到大桥下,从小剧场到咖啡馆,从200名观众到1位观众的戏,他看到了如何从有限中生出无限的创意。他为异想天开的戏剧形式激动,为题材的异彩纷呈而感慨,他要把国外的好戏剧搬运到中国,让中国观众也有机会领略到这些没有上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2012年,他与合伙人水晶创建了“爱丁堡前沿剧展”,这个戏剧品牌让中国观众可以与国际同步看到国外最新的优秀戏剧。作为爱丁堡戏剧在中国最大的平台,他们为国人引进了无数好剧,其中不乏教科书级别的经典,例如《安德鲁与多莉尼》《屋中怪兽》《最后晚餐》《迷失》《看着我倒下》《教室也疯狂》、日本版《西游记》等等。
这些戏剧,拓宽了中国观众的视野,也打破中国戏剧界很多观念桎梏,鼓舞了戏剧创作的观念更新。同时,也让国际剧团借此机会了解中国的观众。最初受到邀请时,许多国际知名剧团对中国有无戏剧市场是存疑的:中国有这样的观众群吗?但演出场面的热烈给了这些国际剧团大大的惊喜,中国观众对小剧场戏剧的热情和极高的文化素养让他们印象深刻,于是,越来越多的海外剧团对来中国演出抱有期待。
如今,“爱丁堡前沿剧展”已牢牢地占据了戏剧观众的心房,小剧场观众中流行着一句话:爱丁堡出品,必属精品,闭着眼睛买票就是了,因为大家相信阅剧无数的袁鸿已经替他们海淘精选过了。
4.创造着不可能
就跟小剧场戏剧的独立精神一样,袁鸿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混圈子,不嘻哈逢迎,也不按套路出牌,敢跟一切不尊重艺术不尊重商业规则的人决裂,但却总能以他的创造力和热忱去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5年袁鸿和他的团队参与发起了杭州西溪国际艺术节,2016年在江苏扬州、南京策展发起江苏戏剧双年展等,而上海艺术新天地,更是其中一个杰作。
新天地在上海的中心,过去是石库门洋房集中的地方,后来是上海老城改建的典范,同时也是人气很旺的商业区。
2016年开始,袁鸿和他的团队在那里策划并组织了一个艺术节,叫“表演艺术新天地”——对表演艺术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同时表演艺术也进到了物理意义上的新天地。他们把石库门弄堂街道街头拐角的地方都变成了剧场。步入其中的人,可能会在书店目睹一场精彩的实验戏剧,也可能会在某个咖啡厅歇脚时成为戏剧的一部分。声音剧场“你听”系列及《耳畔呢喃》、厅堂版昆曲《浮生六记》、博物馆版沉浸式戏剧《朱莉小姐》、户外光影剧场《水面上的梵高》、户外装置巡游戏剧《光影舞马》等剧目令人耳目一新,久久难忘。
表演艺术新天地为这片原本纯粹的商业区注入了文化艺术的灵魂,同时也为这里带来了巨大的人流。创造了淡季收益超过旺季的商业奇迹。这是文化的力量。
这种商业与艺术结合的成功模式,为袁鸿迎来更多合作的邀请。在新天地项目之后,袁鸿又策划了虹桥天地光影艺术节(2016)、上 海 黄 浦 剧 场 开 幕 演 出 季(2016-2017)、上海国际默剧展(2018)、上海大剧院国际小剧场展演(2019)等大型活动,他总是在创造着不可能。
2021年国庆假期,在廊坊丝路艺术中心,袁鸿在7天内推出了100多场演出,廊坊离北京不算近,居然人潮如织,第三天便实现盈利,叫好又叫座。这是袁鸿独有的本事。
5.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建起联系
从戏剧观众到自建平台,从引进交流到策划孵化,中年袁鸿越来越把精力投入到对青年艺术家的培育扶持中。时下与前滩31文化演艺中心联合举办的“前滩31青年艺创计划”,便是为下一代戏剧创作者们提供一个起跳的平台。
策划组织种种大项目大活动,要付出多少精力和心血,常人难以想象。更难想象的是,他为何还有那么多精力和热情亲身投入一部部小戏的制作,为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新奇的、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戏剧体验。
2019年,他参与制作的一部戏,叫《回到车上》,是在一辆公交车上完成的参与性戏剧。公交车票价是100元,公交车就是演出场地。每一场只有32张票,每一个观众都成为其中的参与者,体验了一个超越这个时间段的不可能。《回家》,是2020年6月在上海表演艺术新天地首演的声音剧场作品,票价定为120元,买票进场以后其实是没有演员的,这些花了120块钱的观众变成演员,成为了剧中人,不经意间袁鸿调用一个物件在舞台和观众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随着年纪的增长,他更加注重内容是否有沉淀,是否足够打动人心。比如他最新一部参与制作的戏剧《做妈妈》,便是一部重归写实的家庭戏剧——失亲的父女二人通过一个纸箱妈妈完成了伤痛疗愈,用爱和信任度过人生中至暗时刻,八场戏,尽在一餐一饭中进行,单纯的故事,至简的场景,却深深地吸引了袁鸿。问他选择戏剧的标准,他说“动人”。
舆论场中的袁鸿和真实的袁鸿南辕北辙。外人看袁鸿,高冷、理智、讲原则,不讲情面;真实的袁鸿却是腼腆而感性的。前段时间,袁鸿担任北大剧星风采大赛评委,其中一个名为“撒泼”的剧组用有限的空间做了一个关于“流行病学调查”的戏,触动了袁鸿,“我害怕自己共情,中间几次避免把眼光直射给他们,我就只能闭上眼睛去听……”看过无数的剧,他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柔软和善感。
后记
笔者问他:这么多经历,要不要考虑出书?他回答:“如果你的经验真的很好、值得分享,是可以的。但今天的操作模式迭代很快,所以我的经验不见得会成为现在人的经验。如果对人没有指导作用,就不用写了。”我惊讶于他的质朴与纯粹。
而聊起他这二三十年的成绩,袁鸿更多的是感念他的观众,“我的剧场,我策划的活动,都是观众一张票一张票支持出来的。”但更多的观众感念袁鸿,是他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走上戏剧之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与戏剧结缘,背后是低调的袁鸿。曾在北剧场时期帮工的编剧郑旭特别动情地说:“我非常的幸运,在19岁的时候遇到了这么真实这么勇敢的一个人,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在逆境里也可以木秀于林。”
或许更准确地说,袁鸿和小剧场戏剧是相互成就的,他为推动中国小剧场戏剧发展贡献了能量惊人的一己之力,同时,戏剧本身、充满创造热情的戏剧人,乃至如饥似渴的观众,都给了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体制外的人,作为一个自负盈亏的“个体户”,清瘦的袁鸿经常显得形单影只,但他的热爱、他的情怀、他身上迸发出来的不可思议的能量又让他坚如磐石。
小剧场戏剧走过四十年,袁鸿投身其中近三十年,社会日新月异,然而,他的初心没变,他的理想没走形,他依然为新奇的创造力兴奋,依然为真诚的作品热泪盈眶,依然是那个纯粹热爱戏剧并为之燃烧的文艺青年。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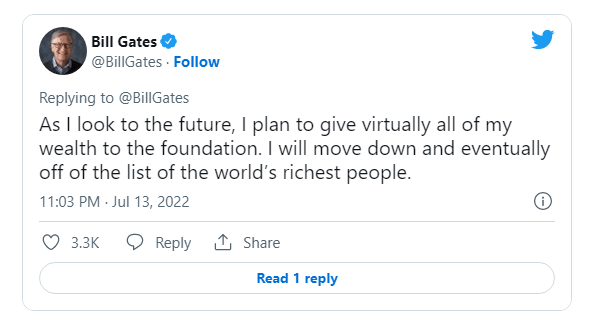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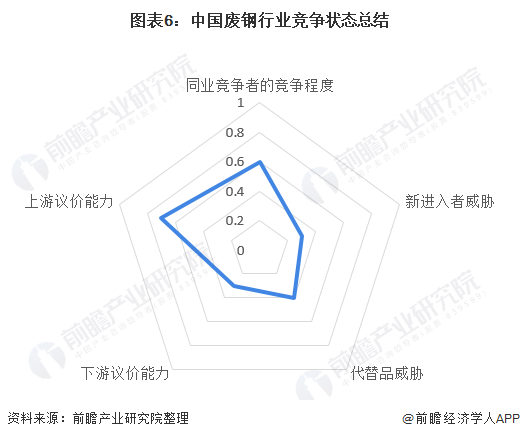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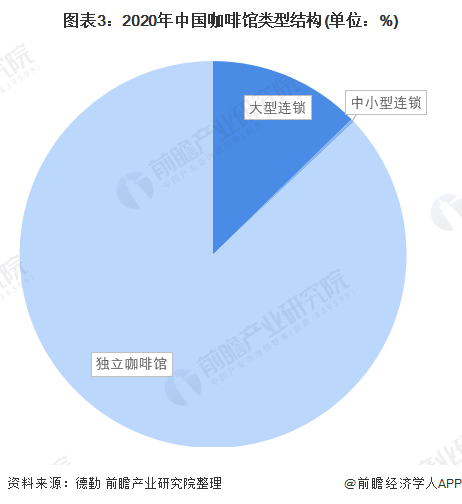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