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敏的文字,我们能够深切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勇于并善于向自我发起挑战的作家,如她在《路人甲与小说家》中所说:“但我并不认为,拥有一个固定的标签式的版图或体系就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某种程度上,我甚至正在试图挣脱这个伟大高尚的传统。”践行此种创作理念,鲁敏的创作风格几经变化:“东坝系列”——“暗疾系列”——“午夜谈性”——“我是谁”的存在之问,直到最近的新作《金色河流》,她的这种探索精神仍丝毫不减,大有流星赶月、前赴后继之势。
《金色河流》前半部分故事的表层,人物尽处一种矛盾纠葛之中:二十余年前,穆有衡私吞了亡友何吉祥的遗产,以此为“第一桶金”发家致富,成为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但未能实现的亡友之托一直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灵魂。而老儿子穆沧、次子王桑,以及干女儿河山,也是他割舍不掉的恩亲与牵挂。
故事的转折与突变来自一份遗嘱的制定与公布。一度叱咤风云的商界传奇穆有衡,终至人生暮年,不仅无奈退出了既有商圈,而且中风瘫痪,饱受疾病的折磨。于此之际,面对有子无人亲切、有朋友却又有愧其嘱托的困境,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想通过一己之力“超度”身边众人。于是,这个精明了一辈子的商人,想出了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高明之“法”——制定一份遗嘱,其内容规定:“在穆有衡去世之前,兄弟两个,不论谁,生出孩子来,即可共同继承全部财产。若两人皆无生养,那么所有的财产将在穆有衡死亡之后,执行全额捐赠。”
这样的嘱托以其金钱之势能,迅速引起了周边至亲、故旧的关注与行动,让原本生活于一潭死水中的人们,围绕这一笔遗产“动”了起来。一纸遗嘱激起千层浪,小说中的人物不仅打破了原有的死寂困境,还在新的价值关联中产生了彼此交织的关系:河山为免于嫁给穆沧,与穆沧、王桑、王桑之妻丁宁发生了交集。王桑一方面为助力哥哥穆沧生养,与河山发生了关联;另一方面又要绵延自身血脉,与妻子丁宁再次恢复了关系。丁宁为了有所生养,需有人经常陪伴去医院“受刑”,于是,她与穆有衡、王桑、穆沧、河山、谢老师都发生了关联。而谢老师追寻河山之母的讯息,与穆有衡、沈红莲、河山、穆沧均产生了关联……
马丁·布伯说,人的价值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显现,这对小说中因一纸遗嘱而勾连起来的人物关系网同样适用。正是因为此网的建立,小说中的人物,才以彼此为“镜”,窥测到了自我人生困境的重要始因。
“镜子”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重要意象。如河山,每遇情绪波动,她就要到卫生间去照照小镜子,从而让自己内心平复,作出有益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无独有偶,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其实也在不停地“寻镜”与“照镜”,只是他们所寻与所照的不是实体性的镜子,而是以“人”为镜。
书中,遗嘱公布之后,人物关系密切交织,这便为故事中的人物提供了良好的以“人”为“镜”的机遇。他们分别在身边之人的镜照下挖掘到了自我困境的镜像成因。如河山,她为免于嫁给傻子穆沧,主动承担起了给穆沧介绍女朋友的工作,在此过程中,她以穆沧为“镜”,找寻到了自我的“镜像”。她认识到了童年经历给她造成的永久性创伤:她长期以来从未真正理解过性与爱的真实情状。再如王桑,他在小说中一直以一个叛逆者的形象出现。王桑自幼苦于父亲的强权干预,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姻,都没有获得过任何自主权。为反抗这种权力的蛮横,他在职场上自我放逐、在婚姻中冷落妻子,事业家庭两不顺。重病的父亲,成为了他人生迷惘之际的一面新“镜子”。人之将死,权利丧失,真情流露,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听着父亲录音带里那一声声声泪俱下的“二子”的呼唤,王桑对亲情、婚姻、事业刹那之间有了全新的认识。
同样,在新的关系网建立之后,王桑之妻丁宁也追忆到了自己的镜像成因。丁宁年轻时对初恋的感觉有一种信仰式的崇拜。在她看来,爱情就是心动、纯洁与美好,但结婚之后的惨状让她感觉冰火两重天。她百般讨好,但事与愿违,直至河山的出现,河山以其自身经历让丁宁意识到爱情远不是初恋那一种可能,而是还有十分复杂的,更为多重的面像。
故事的重要参与者谢老师,也是局中之人,是他的调查对象——沈红莲的“壮举”,让他意识到了自我先前镜像的迷思。以沈红莲为“镜”,谢老师揭开了他自己的镜像成因:二十余年来,他心心念念地想以余生之力揭秘民营企业家的罪恶发家史,殊不知,时长日久,他对穆有衡及其家族成员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无形之中他已成为穆氏家族必不可少的一员……诸此种种,故事中的人物皆以他人为“镜”,向自己记忆中的河流进行了反思性的挖掘,终于探明了自己的镜像成因。于此,“我该何为”的问题完成了质的跨越,至于下一步该为何,这既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存在之思的问题。
正是经由这一阶段的叙事铺垫,故事终于走向了“正题活动”:小说中的人物“老树生新芽”,在对自我的否定之中,完成了正面性的超越。小说的结尾暗示,穆有衡其实早已不再强求个人家庭层面的儿孙之福,而是努力追求着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其实全家福差不多都是一回事儿,所有人的好命歹命都混在一起。他们的孙子就是我们的,我们的票子也是他们的,全在大街上,像河一样,到处流……”
终此,故事在圆满与和谐中缓缓落下了帷幕,如最后一章标题所示:“一物静,万物奔”。反之,“万物奔,一物静”。这是鲁敏对“我该何为”问题的最终解答,也是她对人性自我救赎的再一次深入挖掘。鲁敏一如既往地对自我以及人类精神的困境挥舞起了堂·吉诃德之矛。好的作家需要这样的魄力与勇气!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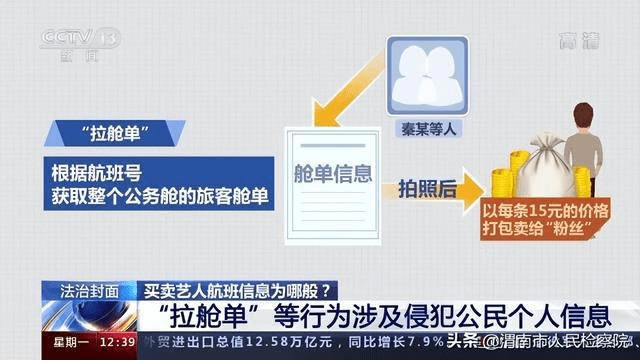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