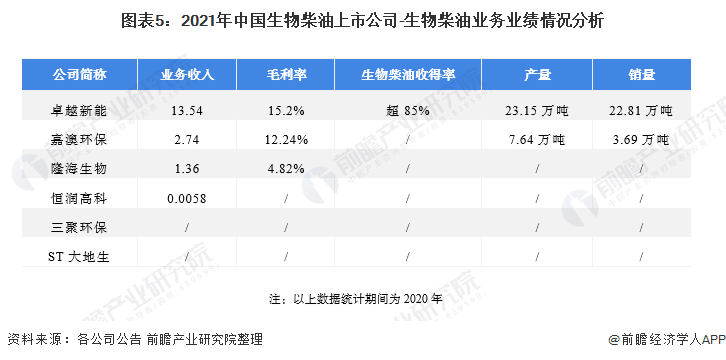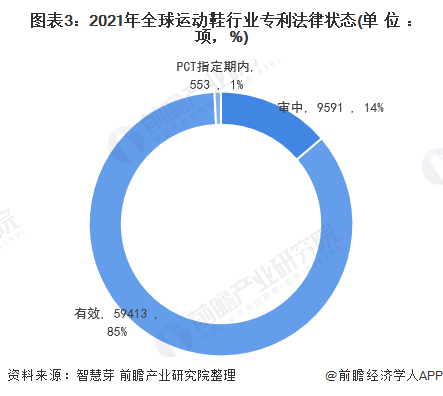郭宗忠
三月,北京市区的迎春花已经盛开,野山桃也爆开了骨朵。这样的季节,仰头望天就能随时看到北归的鸟群——欧椋鸟、寒鸦、大雁的鸟群,都代表着春天的来临,还有一两只落单的苍鹭,也在日夜赶路,追赶着大部队。
郊野公园里,除了玉兰花半开,一两朵野杏花准备着粉红的骨朵,其他的,都好像还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它们肯定有自己的号令。我期待花开,却又怕突然到处繁花似锦,让人目不暇接;还有点惜春的小心思——怕花开的间隙里,春天稍纵即逝。
我还是每天走到郊外的园子里,此时已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它们从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声鸟鸣里浮上眉梢。看吧,月见湖里倒影中的柳树有了绿意,它们枝条上的白头鹎传来了婉转的流水似的叫声,一个冬天白头鹎都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如今,春风荡漾,这是发情期的到来,雄鸟在情不自禁地叫,吸引着雌鸟的关注,这是情歌。有时只是雄鸟自己在唱,如果雌鸟和雄鸟歌声有了呼应,那是两情相悦,在合奏一曲春天的爱情故事。
湖水上空又飞过去一对苍鹭,展开的翅膀好像要覆盖住湖水和大地上的一切。前面的苍鹭边飞边叫,后面的并没有配合,它们朝着西南方向飞了过去。
湖面上有两只绿头野鸭,在湖中间依偎着享受安静的清晨时光,岸边芦苇和蒲苇的残根里,是凤头带着颤音的叫声。我寻找时,一对游到了水中,它们划开的湖水即刻平静下来,并没有形成涟漪。即使它们叫着游过了那对野鸭的身边,野鸭也无动于衷。一只扎入水中,另一只几乎跟着水花,也扎进了水里,也许此时是它们的热恋时刻,在水面上不分离,在水下也要追随在一起。
湖边一排大杨树上的喜鹊突然喳喳喳地叫,原来是最高的枝条上落了十几只乌鸦。这里是喜鹊筑巢的地方,也就是喜鹊的领地,它们对乌鸦的到来感到不适。有大胆的喜鹊朝着乌鸦冲去,但是乌鸦们占据着上风,通过不同叫声传递信号,一会儿工夫,从远处的树林里又飞来了一些喜鹊加入战斗中。但对于乌鸦来说,这并不会构成威胁。它们会对峙多久?不得而知。鸟儿在春天为领地战斗的事不断发生,但是最后,都会找到自己宜居的树林,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冰雪融化之后,湖边稻田里的冻土层也松软了,坑洼里有了积水。园丁们在清理去年的稻茬,然后紧跟着犁开土地,准备播种油菜花。在湖边,春天和农耕是同时开始的,每一个环节的农时,农人和园丁们都心中有数,包括稻田后面的樱桃园里,前些日子在树根施了肥,开始第一次浇灌。
再抬头看看大杨树时,乌鸦们已经消失不见。也许它们只是路过这里而已,让喜鹊们多虑了。喜鹊窝里,每一只喜鹊都在忙碌着,修建去年的老巢,或者重新筑巢,它们一个春天不是在寻找运送树枝的路上,就是在搭建着的巢里规划。你常发现,它们叼着树枝,飞过月见湖上空,倒映着它们劬劳的身影。湖水中也倒映着突然飞过的一群欧椋鸟,还有寒鸦,一队鸟群有的达到千只以上,它们的鸣叫声似乎把湖面震出了波纹。鸟群陆续回归,白天鹅最早到来,然后,紧跟着野鸭到了湖中。灰椋鸟要等到樱桃开花的时候,燕子几乎在清明到来,布谷鸟应该是最晚到来的鸟,它们会在麦子抽穗麦花飘香的时候,突然在夜里啼叫。
去年春天才来到湖边的乌鸫,在这里安了家。不久前一个朋友问我,在他家楼下的小花园里,第一次发现了一只像乌鸦却比乌鸦小的鸟,羽毛全黑只是喙是黄色的。我告诉他那是乌鸫,只一年它们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其实我在想,是这里的环境已经达到了乌鸫栖息的条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为北京带来的水,以及湖边新建的湿地公园,让许多本来在秋天向南方迁徙的鸟儿,还有许多在初春北归的鸟儿,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留在了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如今,越来越多的鸟儿落户月见湖畔已不足为奇,这里这几年新种的千亩油菜花,以及恢复的千亩京西稻田,还有十几个公园连在一起的三山五园园外园的自然景观,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小环境,四季宜人,也四季宜鸟和草木,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和千变万化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在月见湖岸边,不知何时,一群斑鸠在饮水和觅食,它们像在自己的家园里,那样自如自在。喜鹊也来到水边,还有早来的燕雀、白鹡鸰闲庭漫步般在田埂上走着,并不在乎你的存在。
人字形的大雁,是七只,飞过了月见湖的上空。它们认定方向,朝着北方飞去,你似乎听到了它们扇动翅膀的声音,那样有力,有着行军一样的节奏,以至于在湖边突然想朝着它们敬一个礼,你知道,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得住春天勃发的力量了。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