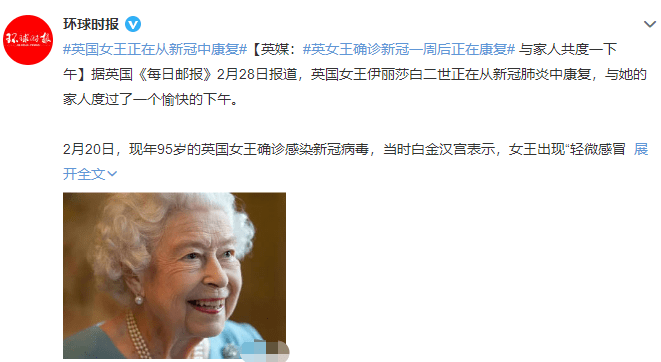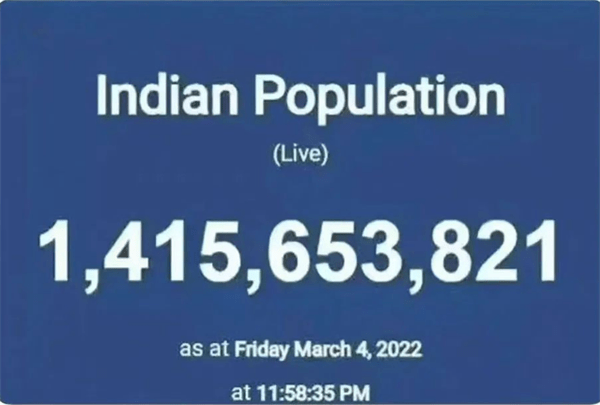晚年鲁迅的言论中,古代话题的背后其实是当下文化难题的显现。考其原因,一是现实的残酷产生了古今对比之意,二是不满意于远离现实的京派学者的审美意识。他的文章多次批评了象牙塔文人对于现实的隔膜。1934年5月所写《儒术》一文,提及儒门读书人在乱世的处世哲学,引用《颜氏家训》的资料嘲讽士大夫的苟活意识,内含着对周作人批评之意;次年所作《“题未定”草(六至九)》讨论陶渊明的作品,直接矫正了朱光潜的审美偏差,以为全面理解作家的作品殊为重要。“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文中还谈及南朝齐诗人谢朓《谢宣城集》,认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京派学者在许多领域不能与现实有效对话,那时候周作人、废名、朱光潜等人的审美意识,忽视的恰是从复杂文脉里寻找精神原色。鲁迅的“暗功夫”冲击了他们的精神围墙,论争里带出的震动,与其说是对古人的重新发现,毋宁说是批判理性在新文学里的一次绽放。
这是显然的: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时候,在前期呼应了疏离桐城派的思潮,重个性,远道统,彰显着一种创造精神;后期则有精神界战士的内力,质疑“纯粹的审美静观”的破绽,审美判断里没有脱离时代语境,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收入眼底,故凝视文本的时候,看到的是社会风气的流转,明暗的聚散。一切文学,都是社会存在的折射,诗文的想象与创造性的表达,也留有时代痕迹。这个看法,与勃兰兑斯、厨川白村、普列汉诺夫的文学思想很像。鲁迅借用不同的资源,激活了传统有意味的部分,他的论述性的文字至今还散着热度,乃因为切入了社会的机体和人性的深处,作家的感觉与学者的见识互为参照,其文学史观念就有了弦外之音,和别样的寄托了。
——孙郁:《鲁迅体味魏晋文脉的方式》,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公众号2021年11月5日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