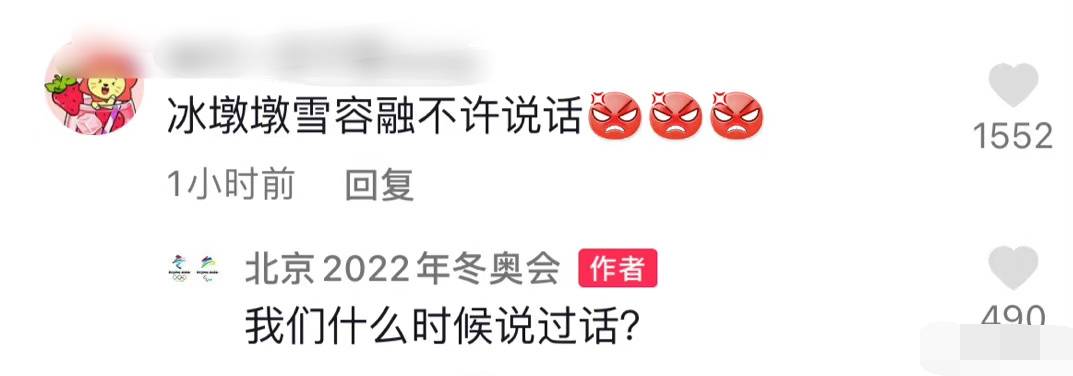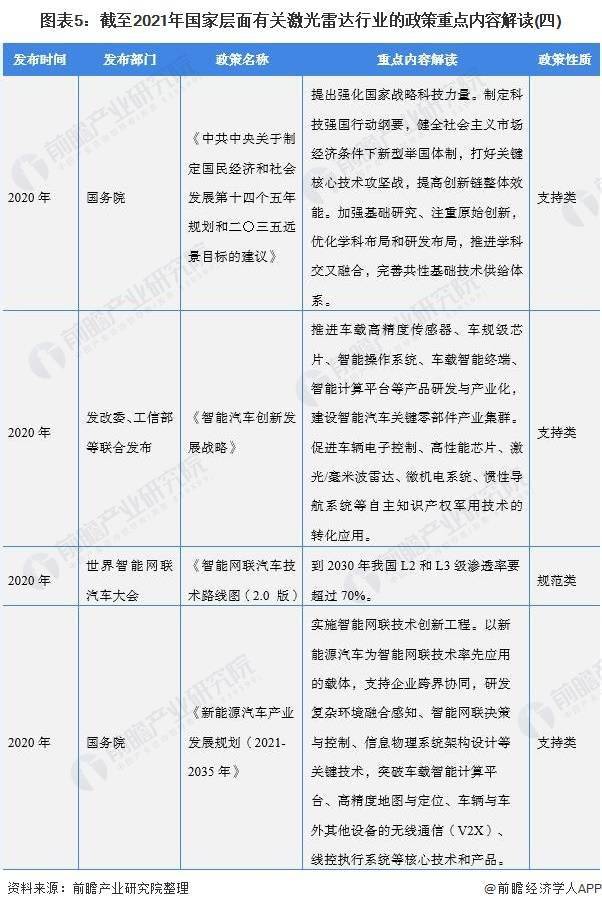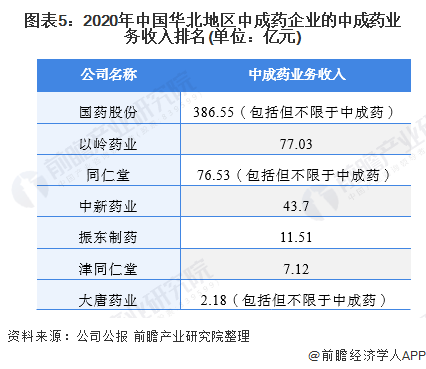族群融合以及主流文化引导下的民族国家统一是世界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普遍、稳定和持久的情况,也是古代世界一些发达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萌生和发展的现象。将文化多元主义简单地看作时尚和理所当然,是一种不严谨的学术态度,需要我们冷静客观地由学术的立场去进行历史分析。
批评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是否认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应该是复杂和丰富的,绝不是要有意缩小或者取消民族国家内部群体的差异性和生动活泼的多样性,而是要将多元文化置于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的语境中。
在过去的40年里,在世界各地的暴力、战争、分裂以及连带的严重人道主义危机背后,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身影。
熔炉模式与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并不神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和政府处理族群关系的工作模式之一,逐渐在西方和世界各地获得多方面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相对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长期使用于族群关系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出现得比较晚,不仅其长时段的效果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观察,其正负效应也应该得到重视。
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代表性学者里面,不少是由善意出发提出社会改革路径。譬如在欧美国家,他们希望纠正非洲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长期遭受的歧视,检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本土原住民进行剥削、压迫和种族灭绝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但由于现代西方国家内部复杂的政治力量对比和经济利益博弈,文化多元主义并不止于社会精英阶层因为负罪感而对历史问题进行的检讨。
文化多元主义遭遇的质疑和重大挑战,恰恰发生在将之运用于处理现代国家族群关系的时候,将之转变为现实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宽容文化差异和鼓励族群平等的思路经常嬗变为人为的、得到政策支持的少数族群诉求甚至特权,以鼓励平等的名义刺激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因为阻碍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譬如反对和敌视主流语言的学习和熟练掌握,伤害到这些族群实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历史上,长时段地看,处理族群关系的文化态度和社会政策并非文化多元主义,而是强调民族国家认同的同化模式和熔炉模式,也就是希望不同的族群认同既定的主流文化,或者共同建立一个包含多个族群传统的新的共同文化。两种模式下的政策导向都是促进一个以公民群体为核心的现代民族的形成。在同化模式下,少数族群会接受和融入主流文化,但是不可避免会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熔炉模式下,各个族群携手创造统一的新民族文化,各自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历史传统。前述两种模式所引导的社会政策都旨在促进社会团结、社会凝聚以及文化传统的交融和多样性。
但是部分学者以及少数族裔群体对这两种模式的认同和支持的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变化。社会学家格莱泽及学者兼政治家莫伊尼汉在1963年合作出版了《在熔炉之外》,1975年两人又共同主编了《族群文化的理论和经验》。到了1980年,历史学家特恩斯特伦等人主编出版了由诸多名家撰写的《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更加系统地研究和展示了美国各个族群的历史和当时的状况。这些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之前被看作是美利坚民族形成最显著特征的熔炉模式受到了更加细致的观察和评估,但不是被否定和贬低。
但在1960年代的纽约,正如格莱泽和莫伊尼汉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所显示的,各个族群的特征以及他们之间的界线仍然明显。他们区分出了五大群体:黑人、波多黎各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纽约,他们指出,至少有四个原因促成了上述这种族群区分的意识:欧洲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遭受的迫害,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以及其他美国人在保留天主教教育独立性问题上的争论,黑人在一战之后开始由南方进入纽约的趋势一直持续,波多黎各人在二战之后大批到来。
但是格莱泽等学者绝不是认为,以熔炉模式(以及一定程度上依托英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同化模式)为路径的美利坚民族塑造失败了。学者经常用来证实熔炉模式成功的例子包括19世纪的德国移民和20世纪的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等天主教移民。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美国其他地方,第三代移民一般都在语言、政治态度和生活习惯上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国家意识强烈的美国人。
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
“合众为一”是不同族群移民所建立的美国所采纳的族群整合模式,是美利坚民族及作为现代国家的美国诞生和发展的成功路径。
格莱泽和莫伊尼汉提醒他们的读者说,“族群”和“族群文化”这样的词汇以及清晰强烈的族群意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罕见的。他们认为,在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得到强化的族群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和撕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政府更多掌握资源的情况下族群认同被当作了争夺政治经济利益的动员工具——以族群多元的名义,以文化多元主义的名义。
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语境里,文化多元主义这一思潮起码具备两大建设性的贡献。一是增加了社会在整体上对种族歧视的敏感度,并因此在道德和态度上有积极的改良,在立法和司法上有相应的举措。二是民众和学者对多样的族群文化遗产有更多的重视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有些学者强调的,一个特定的族群,譬如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天主教移民在深度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进程中,并不会完全丢失由欧洲带来的所有文化习俗。意大利裔美国妇女与父母的关系会普遍比爱尔兰裔的美国妇女更加密切。这一现象脱离了她们各自不同的族群文化遗产就很难解释。
问题是,以文化多元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和处理族群关系有天然的缺陷,尤其在立法和政策受到这一思路影响的时候。格莱泽等学者反对种族歧视,也明确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政策和政治,譬如大学将族裔身份看作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因素之一。他们认为这一导向并非在鼓励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等,而是通过扶植特定少数族群的特权集团,去歧视其他的公民,即所谓“反向的歧视”,其结果是削弱公民和国家整体的凝聚力。
对新移民和弱势的少数族群,强调差异和争取特殊待遇肯定不是进入主流社会的顺畅通道。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者就已经在担忧文化多元主义强化的族群认同会引导一个社会忽略真实的社会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进而伤害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文化多元的名义刻意和人为鼓励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差异,在生活已经多样化到让人眼花缭乱程度的现代社会,往往不是人们自发和自愿的选择,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发展;往往导致对法治和基本社会秩序的蔑视,嬗变为撕裂和分裂的因素;往往与尊重人权和人的个性背道而驰。
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族群问题的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在同样作为多族群国家的美国,英语的绝对主流地位以及移民原住地语言的迅速边缘化,是美利坚民族凝聚力的三大因素之一。英语作为公民们高度认同的共同语言,族群的混居和相互通婚,以及在地理上不存在任何具有族群特性的区域单位,都指向建构美利坚民族的真正强固纽带。
在《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中,潘岳写道,“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这里所说的“情感”,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指民族认同的情感,指超越特定族群的狭隘性以构建国家民族的行动意愿。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引导下,加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才是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坚实基础。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