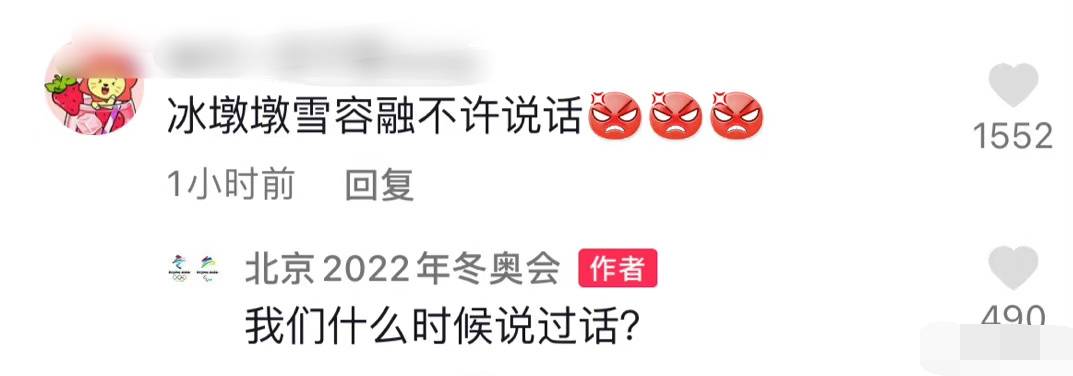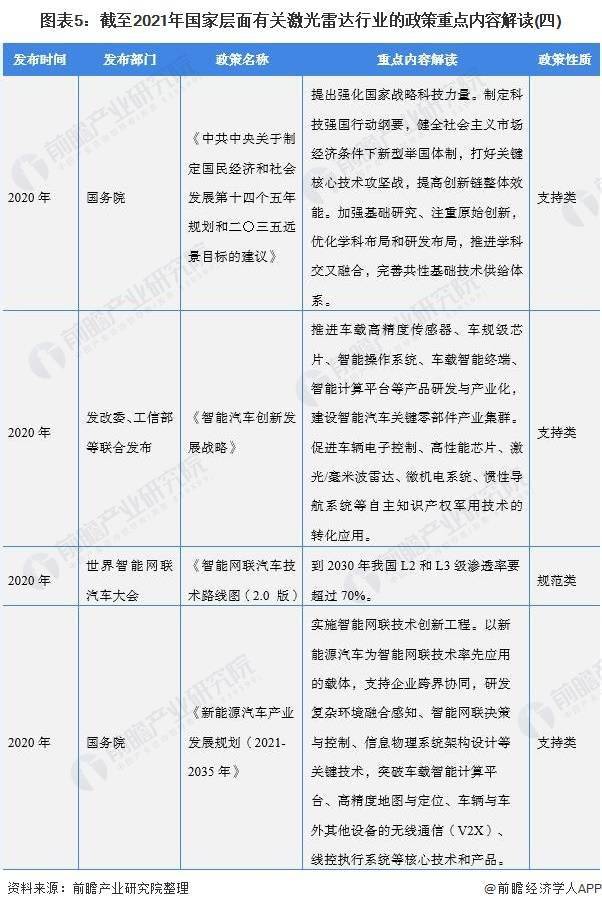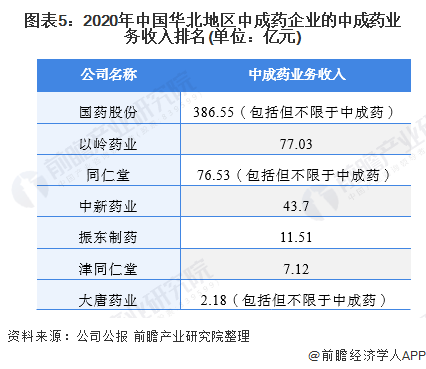“可能《江照黎明》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状态并不完美,但一向喜欢自嘲‘烂片编剧’的我,这次却绝对无法戏谑调侃它为烂片。因为它表达的东西,有沉甸甸的分量。因为它提出的议题,需要板起脸来讨论。希望我们能一起期盼黎明到来……”
正确,但“不好看”
曹笑天在《一个男编剧,写给女性们的告白信》中,这样定性他担纲编剧的作品《江照黎明》:“沉甸甸的表达,严肃讨论的议题”。这两句判词确是精准地抓住了《江照黎明》的定位,女性悬疑题材——作为传统悬疑剧集女性总会沦为工具人的单一想象之扩充,在时代的情绪口上去创造被解读、被救赎、被怜悯、让人期待赞赏的女性角色。
这部讲述了一个努力生活只求安稳的平凡女性,面对丈夫的背叛与恶意,生活的重担和磨难,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自我拯救的故事。将杀妻骗保、家庭暴力、重男轻女、性别偏见、逆来顺受、婚姻困境等最现实系的性别议题全部囊括。女主角李晓楠表面看来拥有让人艳羡的人生——销售冠军、事业有成、夫妻恩爱,然而在生活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随着叙事层层展开,她生活的B面是:晚上桥边炒面赚钱凑钱买房子,老公出轨和人生娃,夜里哮喘发病奄奄一息,老公藏药杀妻,还要顺带参与凶杀案……
李晓楠这一角色将两种矛盾的特质融合得很有说服力:是脆弱又坚韧的、顺从又决绝的女性,她被丈夫算计到开始谋划反戈一击,从猎物变为猎手。可贵之处还在于,她给出了被伤害、被打压、被贬低的女性一个可以“不容忍”的脚本,自救先于被别人拯救。
当我们在社会理论层面不断地推演、探讨“柔弱女性如何自强”这一命题时,无论我们对其自觉与否,一个悖论都横亘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如同让穷人通过理财致富一般,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不曾拥有过的景象。如何变得勇敢?这道题需要一些具象化的示范:主动走出沼泽,去寻找岸边的稻草,而不是顾及自己的狰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消耗,才能有力量度过困境。
《江照黎明》中罗列的直戳时代痛点的性别话题,让理论、议题与解决之间的缝隙被一种故事的可能填补。屏幕前的观众和镜头下的主角,在一些时刻如同交换游戏存档一般,代入自己,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境与剧中人交换,也期待她们代替自己完成一次痛快的反抗。
在这个意义上,《江照黎明》更像是一次“论文体”的创作。有文献综述一般全面的女性困境列举,也有清晰正确的论点论据作台词:在自我成就方面,说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是一种贬低;在亲密关系当中,要对暴力零容忍——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女性通往幸福的路,答案的对与错不在滞后于现实的社会或家长的灌输,而是要自己去思考、不断校准自己的选择,永远要有走出沼泽的勇气。码论点的工整与正确程度,甚至一度让人觉得自己看到了红框黑体加粗加下划线的效果,牺牲的是剧情自然的承转,打破的是《江照黎明》试图立下的于平静中爆发的节奏。
这种“论文体”的问题是:正确,但不够好看。从概念出发组织故事,对社会议题开刀的企图过于明显,塞了太多女性困境的样本进来,到了直给、给标准答案的地步。同样,口号化的台词如果出现的场景、方式不恰当,当剧中医生以发言稿的论调讲出“我也是女性,我相信……”其效果只能是破坏沉浸式观剧的体验。
“正确”离“好看”有多远
也就是说,《江照黎明》同时又延伸出了另一个问题:“正确”与“好看”的距离有多远?换句话说,扛起“永恒的女性引领人类前进”的标语旗帜,打出真实女性困境的话题组合牌能否成为一部文艺作品的“免骂金牌”?
两种标准的不兼容,集中呈现为《江照黎明》口碑的割裂:高分给“看见”社会议题的推动性,低分给剧情的生硬与投机。对《江照黎明》按下五星推荐的观众有真情实感,因为在这里有“女性通往幸福的路在哪里”,有“没有幸福滤镜,直面女性困境”,有“一篇无声的女性战斗檄文”,有“国剧敢拍这渣男,必追到底”——有他们迫切需要喊出的口号,从角色设置到题材创作的维度来看,这样的赞赏是成立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众不买单的悬疑剧观众,称其“故弄玄虚,偏离现实,剧情硬伤”,这些观众的不满意更多的是集中于悬疑剧本身。
当回归到剧情本身,正是因为剧作想要讨论的议题过多,悬疑的节奏屡屡被女性互助的抒情打破,人物设计的不合理与情节设置上的自相矛盾之处便凸显出来。马思纯出演女主角李晓楠,如其影迷朋友的概括:不演美女的马思纯,将灵转换成了“在市井里沥过一遍滚水的温厚”,然而,她太憨了,同时又太壮了,横竖看都像是在夜市里乐观生活、摆摊赚钱的手艺老板娘。于观众处很难具有说服力,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生活在丈夫阴影下、精神被严重折磨的脆弱女人,也很难分辨李晓楠的心宽体胖,到底几分是坚韧几分是苦情。
从悬念的设置上,《江照黎明》与此前林心如制片的《华灯初上》类似,共享同一套模板:以凶杀大戏开局,一条明线猜死者,一条暗线猜凶手,而后用倒叙的方式交代线索,多线叙事汇于一处。在故事铺开的过程中加入创作者所关心的女性议题——《华灯初上》是女性贫困维度的展示,《江照黎明》则是女性主义话题的一把打包。
但《江照黎明》的缺陷在于,导演一边想要与观众“合作”,让观众在悬疑解谜的过程中满足烧脑的快感,但另一方面编剧过浓的说教性又十分不信任观众——谜团不断抛出,但又在无有效信息量的镜头特写中营造悬疑阴云,太多的镜头埋下的伏笔都被揭示是废线。蒙太奇的运用不断抬高观众的胃口,下一秒又轻轻放下。多线叙事需要对群像人物的刻画生动,角色塑造的丰满程度不因戏份多寡而分配。
尤其,剧中女二于红的角色过于工具人了,她的坏实在无逻辑,仅为了推动每每卡住的剧情,这让整个悬疑故事罩上了各种“凑巧感”。“工具人属性过重,需要她体现‘重男轻女’时,她就是可怜的姐姐,需要她体现‘被欺骗的情人’时,她就是宁愿殉情的苦情女,需要她体现女主的难处时,她就是一个毫无脑子、不知感恩的恶毒第三者、报复者……我无法看到于红的悲剧,因为她的悲剧性被工具性消解了。”于红这一角色,又落入了另一种“弱有理”的刻板印象:“我的不幸全是父权制的错,我做一切事情,但我不承担责任。”
“女性+”无疑是当下创作题材的新宠儿,或许是出于挖掘历史中被折叠起的、被忽略的“她们”的命运,或许现实中的问题不断爆发,暗合时下人们情绪出口的爆款往往出自于此。爆款是爆款,好剧是好剧,有时候二者并不百分之百重合——这个问题当下聪明的观众们已充分意识到,然而,“论文体”与好剧之间的差异,却是暂时被藏起来了的一个问题:“正确”议题的野心很大,笔力有限,“社会新闻女主角的戏剧加工”实则是非常生硬地在几个符号里缝合故事。
毕竟,好的影视作品是拷问,而不是给答案。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