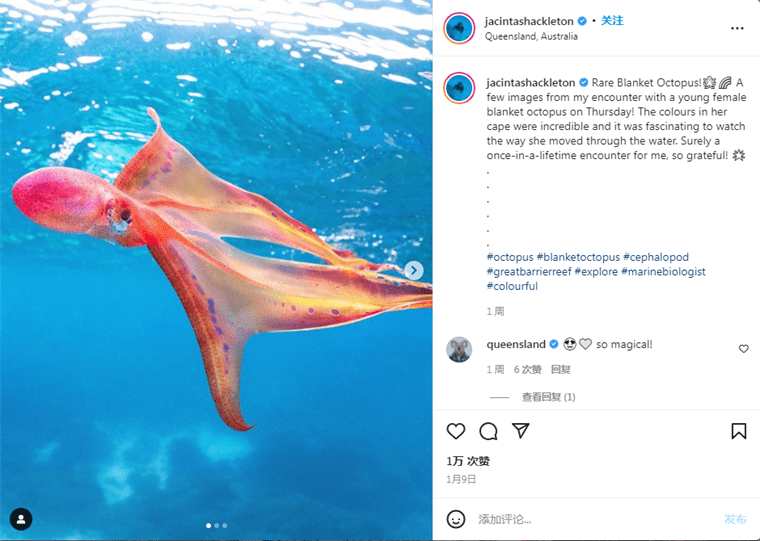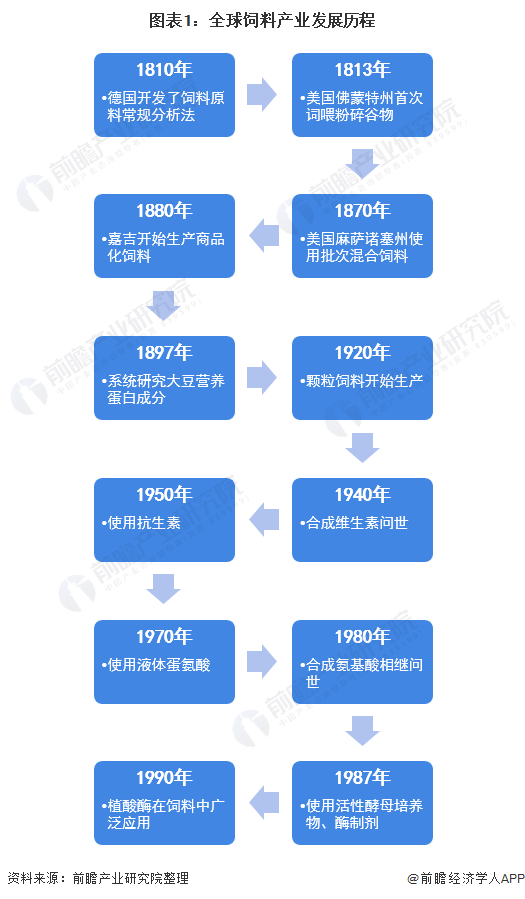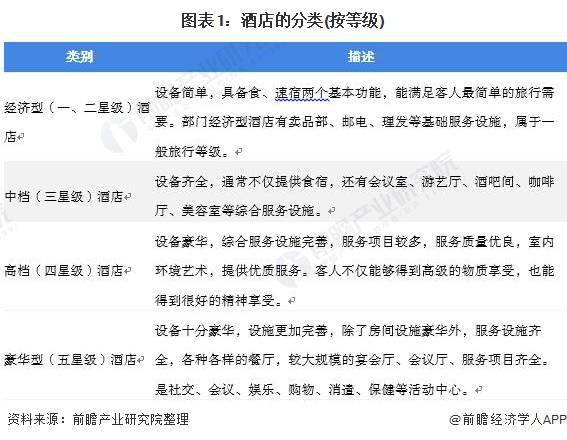飞机驶过蓝天扯出的“白线”慢慢消散,候鸟南北往返的身影转眼即逝;秋收后的大地再次托起苍茫的地平线,搬迁后的村庄重新交予四季轮转……时间流过,谁还记得飞机、候鸟曾掠过这方天空,谁还记得庄稼曾蓬勃了大地、居民曾热闹了村庄?
每念此,便想起泰戈尔那句:“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此刻时空,确无痕迹,但又的确曾来过。飞鸟如此,人亦如此。好在,人是可以留痕的,以资回忆与思念。
以采访者的身份,重回我曾任教三年的马兰村。学校还是那所学校,只不过由初中改为小学。一双双清澈的眸子里,闯入我这位面容沧桑的男人,孩子们有些拘谨,我却莫名亲切。当我亮出在校园里两棵柏树前与学生的合影时,孩子们兴奋起来:“你在这里教过书?”我说:“是呀,你们的爸爸妈妈说不定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柏树、大山会说话,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位城里来的大叔,将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所曾简陋不堪的山区学校。
二十年前的同事老许翻开一本老相册,我在一张张照片中,遇见了年轻的我。老许说:“这孩子的爸爸叫李洋,你教过的。”我端详着键盘前的小男孩,酷似当年的李洋。他又说:“李洋常提起你,说你课教得好,对学生好。只是没考上学,感觉对不住你。”何谈对不住?我曾来过,见证并参与过一群山里娃的成长,何其有幸。如今他们已成人,奔赴山河,还念念不忘当年的老师,知足。
若不是聆听了采访对象邓小岚老师的讲述,还真不清楚我曾来过的马兰村,竟有过一段血泪与荣光交织的峥嵘岁月;真不清楚眼前这位身形瘦弱、眼里有光的老人,竟从父亲邓拓开始,便与这座深山小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讲到邓拓用笔名“马南邨”,来纪念他曾率晋察冀日报社驻扎的马兰村;讲到邓拓题诗“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来纪念在此牺牲的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讲到自己筹建“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来纪念为保护晋察冀日报社,惨遭日寇杀害的19位无辜乡亲……邓老师泪如泉涌。她没有忘记父亲曾工作战斗过的马兰,没有忘记善良英勇的马兰人民,于退休后重返出生地马兰,用“乡村儿童音乐教育”回馈她深深眷恋的村庄。二十多年,青丝变白发,初心不移。
邓老师用她的“回”与“爱”,证明了父亲曾来过,晋察冀日报社曾来过,牺牲的烈士与乡亲曾来过。而将来,数代“马兰小乐队”的成员,又将用怀抱吉他歌唱的形式,证明邓小岚曾在父辈奉献过的马兰,接续奉献过。
采访过不少有故事的人,游览过的不少历史遗迹都让我深受触动。随着年岁愈长,愈发想要留下些什么,以证明我曾来过这纷繁的世界,比如文字、影像、物件,比如在亲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记忆里。于是,我尽可能不间断地填补着虚与实的存储空间,努力用善行,让自己在世间“曾来过”且没“白来过”。
庆幸今生能与文字打上交道,即便一生清苦。曾在政府部门从事过11年文秘工作,写了不计其数的材料。一日重回原单位,向一脸稚嫩的档案管理员报上姓名后,他竟瞪大眼睛盯着我说:“前辈呀!一沓沓文件批阅签上有您的大名,我们不少新人学习过您写的材料。”我忙说:“言重了。”心里却满是欣慰。
爱上写作后,已写了近百万字,记录生活点滴;编辑杂志后,已出版四十期,承载着对文艺的坚守。曾有读者说:“读你的文字,感觉你就是‘透明’的老友。”我深以为然,决心余生以此为业,让后来者从中读懂这座小城,及曾来过小城几十年的我。
越来越“不愿以这种方式认识你”,认识陵园里长长的名录,认识纪念碑上的革命先烈,认识溘然长逝的无双国士,认识无偿捐赠器官延续他人生命的人间天使……惟愿他们默默无闻,也不愿以“这种方式”认识他们。认识已是永别,但他们长存人间的功绩与精神,让我们知道他们曾来过。
总会与日俱增地收藏些于别人无用,于我却珍贵的东西,比如刊发过我文章的报刊、稿费汇款单、差旅各地的车票、电影票根、会议记录本等。偶尔也赠物予人,并嘱其“收好,是个念想”。因为,这些东西聚在一起,就是我曾来过的一生。
“走你走过的路,算不算重逢?”算!我在古城古建、老村老街中漫步缓行,在年代照片、历史典籍中穿越神游,便“重逢”了无数“曾来过”的先人、知己。我之所以将每一步都走得有力有痕,也是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有缘能在交错的时空里“重逢”。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