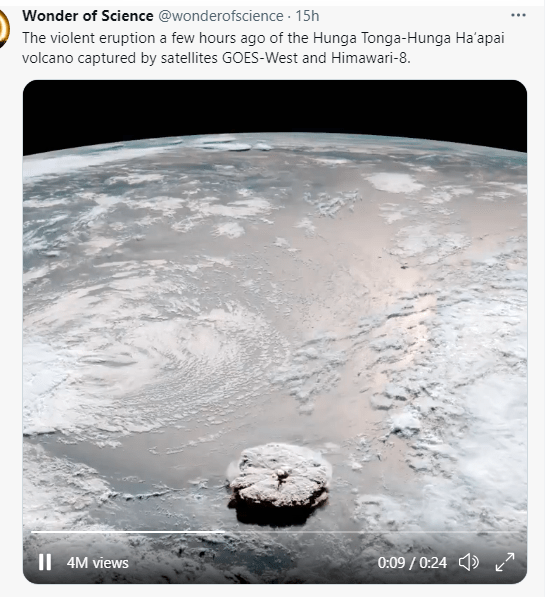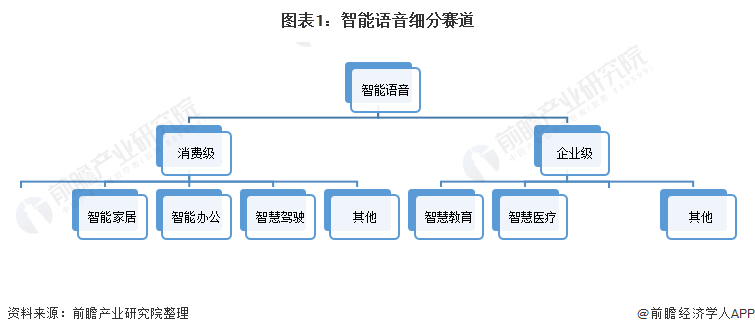采访导演耿军,是1月10日腊八节。之前几天,我看了《东北虎》,喜欢。此文止笔之日,《东北虎》票房过了千万。
“再广阔点,我们寒带电影”
北青报:《东北虎》14日上映,对于还没有看过这个片子的人,您最想怎么介绍您的片子,有您最喜欢的表达吗?
耿军:这个电影在剧本阶段,是一个从仇恨走向宽容的故事。电影拍完之后,它亮出一个问题可以跟观众互动——是仇恨的力量大还是宽容的力量大?当然里边还有那些黑色幽默的东西、有趣的人物,再有就是我们在环境中生存的这种不适,我是不适者,那我们不适者在这个环境里应该怎么办?
那有不适者就有适者,就是适应这个环境的。我一直是一个不适者,就经常会面对现实带来的尴尬,那些尴尬又能产生故事里面的幽默感。黄建新老师说:“能拍黑色幽默的人都是心特别柔软、特别善良的人。”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前两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软化一下心灵吧”,因为艺术作品无论是小说、音乐还是电影,某一方面它是让你短暂放弃掉现实,跟我们的主人公一起生活两个小时,软化一下心灵。
北青报:真好。《东北虎》去年就传过要上映,等到这会儿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噢,虎年了,所以这是《东北虎》上映的理由。但现在我又多了一个想法,从我自己看的体验,我觉得它其实挺适合过年看的,它其实是个挺温暖人心的电影。
耿军:我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吧——有一个真诚表达的前提,去说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北青报:有意思,一个东北最北地方发生的故事,最后讲出了温暖人心。我看资料,电影是在年尾年头时间拍的,那地方那个时候该冷死了吧?
耿军:嗯,我们是2018年12月到2019年1月,这两个月时间拍的。黑龙江正是最冷的时候,天黑得也早,下午三点半黑天了,收工到酒店四点来钟。他们说吃完饭再喝两顿酒,一共三个局,回来一看十点半。北欧的那个纬度嘛。
北青报:您说过您的电影叫寒带电影,是吧?
耿军:对,他们老说“作为东北电影”如何如何,我说:“再广阔点,我们寒带电影。”
北青报:之前记得是看《一代宗师》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好像咱们很少有拍北方、拍冰雪拍得特别好的。直到《一代宗师》东北那些戏、送葬那场,还有火车站那场对决,把冰雪表现得特别好看。我觉得您的电影,也有“寒带”的那种感觉。
耿军:这种环境呢,它有机会拍得特别唯美。当然我们没有追求唯美,我们追求的是生活质感和那个环境本身,就气候对人的浸染,我们要拍的是这方面的肌理。《一代宗师》那种唯美我也特别喜欢,那是故事需要。我们也是因为故事需要,不需要这种。
“伤感没意思”
北青报:提到东北,这些年有“东北文艺复兴”,有“黑龙江省三亚市”,鹤岗也挺出名的,“五万块在鹤岗买套房”什么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在吸引您一直讲它的故事?
耿军:我特别喜欢鹤岗的冬天,冰雪把黑土地变成白色,大家在街上都缩着。晚饭过后,大家走路开始软绵绵的,是因为喝了酒。喝了酒之后这个世界开始柔和了,走在街上看着街上的人也开始顺眼了。就觉得这些人虽然擦肩而过,但是仿佛是熟人,生活里边那种东北特质的东西,挺让人上瘾的。
而且鹤岗这个地方,我儿童少年青年期在那儿度过,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乐园。因为小时候玩得特别高兴,没有被学业束缚,因为我不是个好学生;完了家里边又管理得比较疏忽,我们没有发生人身安全问题,就已经算幸运儿了。因为童年玩得特别高兴,所以情感寄托就在那儿,那个地方你想起来亲切。童年过得高兴对创作也特别有帮助,如果童年过得不好的话,我觉得想象力、创造力这些东西都会被抹杀。我们童年过得真是天真烂漫,大傻子似的,就是野狍子。
北青报:嗯,那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从您眼里看过去,您并没有看到它的衰败或者是绝望或者……
耿军:衰败这件事,它不单单是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很多地方。它不是一个局部问题,是一个广阔的问题。事物由新到旧的更迭,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它有鼎盛就有衰败,完了之后下一个鼎盛期什么时候来,它可能有内在的规律,或者是不太好解释的那样一个东西。这种事它会让你触景生情,但它又是自然规律,树木一年四季更替、枯荣,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它曾经那么鼎盛,那么繁华,然后它逐渐走向了这个地方的中年。那是不是暮年也快到了?暮年到来之后,它是不是要重新焕发它的活力?不知道。但我希望是这样的。
北青报:那您真的还蛮……乐观的,这个词很俗啊,但是……
耿军:我其实是骨子里边挺悲观的一个人。当然这个东西,像我电影里边的台词一样——“伤感没意思”,但前提是伤感哪。
北青报:东北近几十年的经历,给大家印象是一个蛮悲情的地方,或者在很多影视表现里,可能是比较暴力的地方。所以我挺喜欢您这个片子,您写出了它别的那一面。
耿军:特别正常的一面。它既现实又荒诞,又有诗意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审美观。影视作品其实并不会对一个城市怎么样,你比如说我们看香港枪战片、警匪片,会觉得那儿是一个特别乱的地儿,到了香港以后发现,天哪!那都是电影里边弄的。
“听说你不太好,我来看看你”
北青报:说实在的,我之前对一些现实题材电影是有保留的。尤其有一堆四个字名字的,感觉看得挺受伤——都挺绝望、挺黑暗,挺凄风苦雨的,好像治安也不太好,似乎一写现实,就非得看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可是《东北虎》里我看到了温情,特别您那个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轻的。
耿军:有温暖的色彩,有浪漫的色彩。
北青报:对对。尤其里边小二那个角色,我觉得特别喜欢,“听说你不太好,我来看看你。”“给你带来一只风筝,带鱼特别特别好吃。”
耿军:特别暖。小二是来救马千里的。马千里因为举债陷入自己的人生绝境,完了又被徐东(就是章宇饰演的那个角色)追讨杀狗之仇。那么大一个老板,他以前资产是正数,带领亲属一起挣钱,亲属肯定也挣到过钱,完了现在是正数变负数。这个时候小二的出现,其实是拉了他一把。那么多亲属都围着他讨债,完了只有这个之前在他工地上过班的人,带着最大的礼——500块钱、带鱼,还有一只风筝去看他。
北青报:后面卖梯子那个也是小二吗?
耿军:也是。小二的前提是他在马经理那儿打过零散的工。楼房卖不出去,工程款也没有结,那其他人的工钱都结了吗?马千里上去就问:“小二,我不欠你钱吧?”那这帮人,现在这么不景气,他们怎么度日呢?可能会把用不到的东西卖掉,无论是卖梯子还是卖脚手架的一部分,在他这个人物身上都恰如其分。
小二卖的是梯子,电影里小二一共是两个重要的道具,都是往高了走的。马千里这帮人,曾经混得比较牛、生活秩序里如鱼得水的人,是往低走的,而小二的风筝和梯子,是往高了走的。其实是我寄托了一个,就大家站得高一点,稍微看一看远处,我们现在的这种苦恼是不是能打开一点?
北青报: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现在大家的情绪有点往下走,特别是两年的疫情下来。那电影里的人,马经理天天被人追债,车也被砸了,那是很绝望的一个境遇;章宇演的徐东,狗被人吃了,婚外恋情被老婆拿了,也蛮狼狈的。但即便这样,您电影最后的那句话是——
耿军:“我们一起挺过今天,明天可有意思了。”是妈妈跟他说的话。
北青报:这是我很喜欢这个片子的地方,再残酷的现实或者怎么样,作为一个电影除了让大家共情……
耿军:得有个出口,得有个抓手。要不你没着没落的,大家内心里会觉得特别空。
“这么露怯的事我就不干了”
北青报:那这种信念或者这种精神,在您身上我特别想找到它的来路。我去看了你在“一席”讲自己的故事,您作为一个养鸡家庭的文艺青年,到北京住地下室,什么东西都长毛那些经历,包括雪夜从北四环走到东四环,我体会您也是非常不容易走过来的。那您是怎么还保持了这种特质,是东北人天性里的某些东西吗,还是怎么样?
耿军:我自己后来也想了一下这件事是什么,是我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就果断放弃——因为个人能力付出、追求也达不到的,我就主动放弃了。比如说一天里边有三件事,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这件事我就不做了,完了我去做那两件我能做到的事。
所以无论是现实层面,比如现实生活里面最常见的,我表弟,1988年的,比我小12岁,他在三河买了一个房子。他交了首付,完了每个月要还五六千块钱,而他每个月也就挣六七千。那他回家的时候,会感觉他父亲没有给他拿钱,就特别怨恨自己的父亲。我是不干这样的事的。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买个房子拴住我呢?我是一个来京务工者,我为什么要让这些物质的东西把我给……现实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向你撞来,我是躲开的,我不会跟它撞的。我觉得那些东西,前提它不是我要去努力的东西,所以我就果断放弃,给自己一个自由。
你像住地下室或者什么,我觉得对于一个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专长的来京务工人员,这样是正常生活。地下室住的不光是我自己,好多人都住地下室。我们住地下室的邻居里边有一个姓刘的老师,他是教英语的,还是上海人。上海人上北京住地下室,我是搞不明白的。他可能也搞不明白我这么年轻的人怎么也住地下室。我们互相礼貌点头,完了偶尔,他把一本杂志拿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小耿”,我一看,我说“这是我们那个影视专业杂志”。他说“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还有搞音乐的,我们合租在地下室里边。他们想搞自己的原创是很难的,反正他们晚上就要去唱《东方斯卡拉》,需要夜场挣三百五百的,打车都不舍得,就买一电瓶车。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就是来京务工人员的一个基础生活,我倒没有觉得这事有多么苦啊什么的,挺正常。
因为家里边父母他们养鸡、卖鸡蛋,爸妈两人差不多养2000只鸡,就是这种朴素家庭,他们吃苦耐劳那样儿,对我影响也挺大的。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摆脱——也不是说没有摆脱,这不叫摆脱,叫什么呢?
北青报:改变?
耿军:就是那种比较朴素的生活吧,一打开衣柜,十多年以前的衣服都在里边呢,你也不穿,你也不舍得扔,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送他,完了就在那儿放着。就是那个环境里出来的人,说有什么多大的变化不太可能。所以那个东西就是家庭环境影响。
北青报:家庭影响让您可以安之若素于物质比较贫瘠的生活,那有些人他们会,比如白岩松说过大学有些从农村来的同学,他们往往是最早穿上西服和皮鞋的,因为他没有过,所以他会向往。但您好像不是,那我想也许是有别的很笃定的东西,让你觉得你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实现您的境遇改善或者是阶层跃升?
耿军:虚荣心这件事儿,对于青年人,20岁来北京的都有。但是我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我们这种小地方人来到这儿,穿着皮鞋穿着西装,就会觉得特别奇怪,完了之后我说“这么露怯的事我就不干了”。城里边的人如果不是有商务要求的话,大家穿的其实都挺休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维斯、班尼路、李宁鞋。
“我爸说我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
北青报:我前一阵儿采访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那时他就跟我提到您。那像您这个经历,在业界大家也会认为还是蛮传奇的,对吧?首先您没有正式进过电影学院(我知道您去旁听了很多课),那样至少您就失去了一个平台和那些同学,就没进到圈里;您也没有什么家学,也不像陈凯歌、田壮壮有那样的爸爸妈妈。那您能够拍出来,我想在很多人看来还是个挺励志故事。我知道您挺不喜欢“励志”这个事儿的。
耿军:励志没问题,不“鸡汤”就好。我是1976年生人,完完全全是因为赶上了2000年这个时代,就是DV和数码在民间开始普及,我们踩到了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才有机会拍电影。要不然,我可能能做一编剧,但也是挣不到钱的。因为我的剧本也不太容易卖出去,人家看着都觉得这玩意没什么价值,不是那种商业类型需求,我没有能力写那样的剧本。所以我写的剧本基本上就是我拍。我2000年初的时候动过就是做编剧、靠写剧本为生这个念头,但是没成。
北青报:很难。我那会儿采访写《孔雀》《立春》的李樯,他算做编剧很成功的了。
耿军:他写得太好了。
北青报:那他跟我讲他原来那个经历,也是九死一生,写了又拍不成,本来要拍了又没钱这种。
耿军:对,因为大家年龄差不了多少岁。然后它有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就是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最基础的生活的这些东西,对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普通人,那个杀伤力都是巨大的。就你要挣钱养家,你要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维持家庭这件事上,那基本上就会耗尽一个人全部的力气,家庭生活才能过得像那么回事。我是什么?我是这件事没办。我没有结婚、生子、买房、买车,我没办这件事,我只干了这么点电影的事。
在某些点上,就是在我父母眼里边,我的人生其实是一个……
北青报:不完整的?
耿军:就挺失败的吧。我认,这件事我认。他们说这件事我是认的,确实,我们同学里边20岁生孩子的,他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爸说你耽误了一代人,这事我认,确实是啊。
北青报:那我觉得有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您在这条路上走得还是蛮坚定的。就像您最早拍的那个片,您自己也说差得不行,别人也说差什么的,但您还是继续走下去了。我觉得您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吧?
耿军:我其实在某些点儿上来说,是一个没有什么人生规划、没有什么计划性的一个人。完了我就觉得影像、电影讲故事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挺有吸引力的。我就试着用自己的能力,调动自己身边的资源,这帮好朋友能帮我演,还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摄影师、录音师,就试着用最低成本的方式拍。运气还不错,每拍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本身的运气和我个人的运气还都不错,完了就能达到持续创作的那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持续创作。
北青报:您说的运气,包括……
耿军:比如说去电影节、发行收回成本,这些事儿。也包括认识张献民老师。我在电影这件事上一共是两个老师,一个张献民老师,还有一个是跟我合作编剧的刘兵老师。他们对电影的认知更宽广,我是由着自己的兴趣走的。跟他们在一起合作,就会让我由着自己的兴趣走,把那种底子保留住,让叙事、形式,在个人认知和能力基础上,还有艺术的审美上能再往前走一点。张献民老师、刘兵老师在这点上其实是帮助、推动,非常重要。
“生活普通,只是需要大面积的安静”
北青报:《东北虎》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音乐。除了片尾曲挺摇滚,其他配乐还都挺洋的。
耿军:是啊,我们其实没有做顺拐的音乐。顺拐的音乐,比如说民族风那种音乐很好听,但它不适合我们的电影。我们需要把听觉这个空间打开,完了之后要让土地、人物、环境,跟那个听觉同时发酵。我们其实在这个点上做了很详细的讨论,我们要做得稍微洋气一点。但我们不需要那种特别大的音乐,我们需要小一点、跟着人的内心走的音乐。
北青报:好的。那我很感兴趣一点,您的素养是怎么来完成的?我知道您到电影学院去听过徐皓峰的课,是吧?
耿军:对,我在电影学院听了好多人的课。徐皓峰老师我很喜欢他的课,他的“视听语言”讲得特别精彩。我也喜欢他的写作,他的书写得也好。我们也认识,人特别有魅力。
北青报:那您平时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的电影、书或者听什么音乐呢?
耿军:我从小就听广播嘛。我在家里边电视是不打开的,早上起来就先把广播打开,什么915、887、974啊。最大的滋养可能来自于纯文学的阅读吧。我喜欢看小说,其他的工具书我都不看,我就是喜欢看纯文学类的东西。电影,其实到现在来说也不是特别挑食,因为好电影太多了,没看过的电影就是新电影,现在看电影又那么便捷。看电影的时间可能没有阅读的时间长。
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做编剧的,会特别留意生活里边人和人之间的细节,有时候也会偶尔记录一点。其实生活本身还是挺普通的吧,唯一跟其他人有区别的是,可能需要大面积的安静。就是可能这一大段时间没干什么,但是也需要这种大面积的安静的时间。
北青报:那像您现在越来越算是一个成功的导演了,可能身边围绕着工作室的人或者是班底的人,还有机会去观察生活吗?
耿军:我们在一起时间很少的。工作的时候在一起,平时连聚会都很少,大家相处得也很好,剩下的时间还是属于自己。我身边作家朋友比较多,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比如东北的蓝石,沈阳那个作家。他周边就是北京这边的狗子、张弛。这帮人都非常有趣,是60后那拨人。他们聊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很多都是没听过没见过的。跟他们坐一起不用干吗,听他们聊天就行。
北青报:那像您喜欢读谁的小说呢?
耿军:我最近在看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姜,他是纯文学科幻,写得太好了。前段时间还看了余华的《文城》,村上春树的两本短篇小说集。我2021年阅读特别失败,4月份的时候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看了,到现在一本也没看。看了好多本短篇小说集。
关键词:
 首页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