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木心先生于2011年12月21日因病逝世,距今已十年。本文是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志强为纪念木心先生逝世十周年所作文章。
诗人的典型气质
木心先生二〇〇六年回国,到他去世,这中间我见过他三次。
前两次是在他临时下榻的乌镇通安宾馆,后一次是在晚晴小筑(今之木心故居)。拜访时间有长有短,印象都很深刻。
记得他刚回国时身体状况不大好,腿脚不便,走路用拐杖。半年后就恢复得很好了,气色红润,身板硬朗,坐着谈话时,阳光照着他的脸,白发奕奕闪亮,婴儿脚掌一样的大耳朵红彤彤的半透明,让人看着很是高兴。
晚晴小筑那次,他给我看画,将几十幅画作(多半是石印画)一张一张在地上铺开,他蹲下,起立,把画纸拿来拿去,一点都不显得疲累。
分别时送我到院门外的公路上,连外套也不穿;说下次见面聊。谁知隔年惊闻噩耗,先生遽尔辞世,和读者和亲友永别了。
他在诗中写道:“永恒便是无尽的呆愕。”那么,现在,永恒归属于他,呆愕则留给爱他、亲近他、不相信从此永别的那些人了。
时光飞逝,转眼就是十周年祭。
这十年里,读他的书,讲他,怀念他。他活着时,去拜访的次数少,他去世后,也未写过什么文章纪念,想来就觉得愧疚。木心先生把我当作晚辈中的一个朋友,交往不多却少有隔阂。
说起我对他的回忆,说的就是他老人家的举止言谈,有点像客厅轶事见闻之类。除了因为交往少,私下了解有限,我想这主要还是基于他诗人的典型气质或属性吧。
诗人是灵长类物种中的语言寄生物;可以说诗人是语言的在场,正如商人是金钱的在场,政客是权力的在场。回想起和木心先生见面时的点点滴滴,眼前浮现的便是他的言谈、神态和语气,而那是十分令人难忘的。
他的思想非常活跃,妙语连珠,睿智而诙谐;跟他老人家交谈,没说几句就像坐热气球一样把你往上提升,文学、音乐、哲学……,梭罗、瓦格纳、佛朗克、哈代……,不知不觉就会谈上数小时,没有寒暄和客套,每次都是这样;好像他一生都是在从事这场纯粹的精神之旅,与人交谈是长途跋涉中的小憩,而他人的疲倦不支则会令他惊讶。
记得初次见面他就问我,中国古代画家中喜欢哪一位?我回答说是“倪瓒”。他颔首,说:“string quartet(弦乐四重奏)。” 便转身做了一个演奏音乐的动作,补充说:“他只使用小型乐器。”然后比比划划,说前景、近景、中景、远景相当于四种乐器的配合,等等。他的比喻令人耳目一新,而他说话的神态有几分孩子气。
印象中,他开口前总是笑吟吟地眨一下眼,好像是自己心里先乐了;表情略带腼腆,并无预想中的威严。他袖手侧身,轻言细语地“掼戏话”(这是我们湖州、嘉兴一带的方言,说俏皮话的意思),眼睛眨巴着向一侧看,像是在看他说出来的句子,盈盈然似有光彩。我记不住他说过的话,太多了,记不下来。郁达夫先生的文章里说,每次拜访鲁迅先生,回去路上想起先生说的某句话,都还忍不住要笑。我拜访木心先生也有这种体会。
有一次交谈时谈到鲁迅先生,他起身像是去洗手间,侧过脸用上海话咕哝道:“同伊好比啊!”(跟他能比吗?)
说起五四文学,他总是谈周氏兄弟,尊他们为大诗人,认为别具一格的高超文体是一个方面,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心性和思想。
说起诗歌,他说最称心的还是阿波利奈尔的无标点自由体诗,旧体的格律诗可以玩,但也就那么一点意思,平仄对仗傻里傻气的。
问他对当代诗人的评价,他说:“顾城好。”
问到绘画方面,他说:“我赞赏安塞姆·基弗、卢西恩·弗洛伊德、安东尼·塔皮埃斯……”
有一次他问我怎么看张爱玲,我回答说,人一格言二散文三小说四。
他听罢哂笑一声,默然不予认同。
他不喜欢争论,从不大声说话,交谈时很注意倾听。如果有什么说法当众忤逆了他的自尊或信条,他会昂然掉过头去,下巴颏扬起。
他一根接一根抽烟,烟灰长长的不去弹落,掉在了毛衣上也不掸拂。像波德莱尔,他衣着考究,精于修饰。言谈总是委婉而诚挚。深黑的瞳仁像光滑的丝绒。年逾八旬,他的眼睛还是亮的,清亮明净,富有神采。他满足了我平生的一个愿望:和诗人卓越的化身交谈。这是我的荣幸。可惜几次见面都未留下一张合影做个纪念。
最后一次见面告辞时,他让我等一下,说是给我看个东西。他去楼上卧室,过了一会儿拿着一张小纸片下来,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分享从新闻纸上剪下的一幅尼采临终前的肖像。我见过这张相片,尼采的胡须像皮鞋刷子,衣衫像理发店的罩布。木心先生用吴侬软语的普通话轻声说道:
“你看,他尽管是发疯了,可还是那么的伟大。”
这平平常常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是说,记忆中出现最多的是这个细节;他的语气、神态(那不可腐蚀的纯真),当时客厅里的光线,小镇午后惫懒的阳光,都还记得真切。
象征主义的“入”和“出”
我在世纪之交开始接触木心先生的作品,是朋友周江林推荐我看的;此前从未听说过木心这个名字。也就是说,木心先生归国之前我就读他作品(复印件)、听闻其传说了。他是我心目中的大人物。
阅读木心是我生活中一件可纪念的事。如果没见过木心先生本人,我会觉得遗憾,但这也许不是最重要;如果他的著作到现在都没有在我案头出现,那就是难以设想的了。
我习惯于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设置距离;就是说你喜欢一个作家,读其作品就够了,不一定要和作者本人见面。作品是最好的媒介。和作家打交道,要看到的不是肉身而是作品。好作家一定是活在其作品中,应该是每个细胞都存活在里面。说得荒谬些,作家是活着还是死去,终究是无关紧要的,凡人终有一死,重要的是其作品在读者手中流传,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灵魂不灭,伴随人们的阅读而在世上长存。
话是这么说,但我还是希望多几次拜访,记录木心先生的言谈。缺少交谈和记录,有些言论就流失了。木心先生要是再能多活几年,他对文学、绘画、音乐的见解就一定还会源源不断地表达出来,给人滋补和启迪,想到这一点就会为他的逝去而痛惜。
记得他曾给我解释局部投影何以对绘画鉴赏是一个福祉,当时我没有完全听明白,没有弄懂他所说的“狂喜”是怎样一种感觉。也就是说,不是某个概念,而是其言语所指的感觉和体验。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是我希望得到求证和解释的。但是很遗憾,不会再有机会了。
他在著作中这样评论瓦格纳:
“瓦格纳的音乐不是性感的常识剧情,是欲与欲的织锦,非人的意志是经,人的意志是纬,时间是梭,音乐家有奇妙的编纂法,渐渐就艳丽得苍凉了,不能不缥缈高举,波腾而去。被遗弃的倒是累累肉体,快乐而绝望的素材——自来信仰与悔恨成正比,悔恨是零乱的,整齐了,就是信仰。”
类似的段落也是我想求证的。木心先生所处的时代应该还不具备条件,大量聆听瓦格纳的歌剧录音,他这番高见卓识非资深乐迷而不能道,即便是资深乐迷通常也是讲不出的,我自然感到佩服。见面时他谈到瓦格纳,谈的是《帕西法尔》和“返璞归真”之间的关系。寥寥数言,言简意深,留给听者自己去体会。那么,求证什么呢?好像也没什么需要当面求证的吧。
如果作家尊重读者,就不应该去迁就读者,他只需真确地表达其感觉和观念,在真确的意义上为其感觉和观念赋形,其余的留给读者自己去做就可以了。木心先生的表达,无论是言谈还是书写,其对真确性的追求是很不一般的。
文学中对真确性的强调,通常是属于古典主义的范畴,讲的是恰当、含蓄和明晰。木心先生的风格并不属于古典主义,更像是作为年龄之结果,或者说是作为其浪漫精神之反拨的一个表现。
他在诗中写道:“能做的是长途跋涉之后的归真返璞。”
他谈歌剧《帕西法尔》序曲也是在说这个意思;无疑是注入了他自己的心得体会。我会把“归真返璞”的命题和他的一句诗(出自《象征关》)放在一起看。诗云:
“不入象征主义非夫也,出不了象征主义亦不是脚色。”
拿这个句子作注脚,也许是窄化了他所谓的“归真返璞”的意涵。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是可见的。它指出作家的“长途跋涉”的起点,也指明其精神、美学的演化进路,他在艺术上的化入、化出(如何化出也许是更有意思的命题),因此显得耐人寻味。
木心先生的文学起点是象征主义,波德莱尔、瓦莱里、纪德等。他的阅读十分广泛(《文学回忆录》便是一个例证),包括莎士比亚、拜伦、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以及中古波斯、阿拉伯文学,等等;所受的影响是驳杂的,不能只归结到一个方面。但是作为诗人木心的发端和成长,象征主义是关键。他的诗作之精彩和难解,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象征主义的诗学特质:意象、隐喻、典故等组合,不是用来传达约定俗成的主题,而是追求词语独特的联想和张力;诗人的表达本身即是主题,表达从想象界到实在界的坠落,以及两者之间的参差与竞争,这构成了其诗歌主题最有活力的一面,不管风格是隐晦还是显白,都和波德莱尔、叶芝等人的创作息息相通。木心先生的绘画应该也是同出一源,即体现十九世纪晚期欧洲艺术的转向和主张,认为绘画是想象的结果,而非视觉印象之再现。
以《剑桥怀博尔赫斯》为例。这首诗的主旨并不复杂,但是其意象和典故织成的象征是一种个人化的象征,彻底的解码也就变得困难。诗的第一句——“一从没有反面的正面来/另一来自没有正面的反面”,绕口令式的句法无疑给阅读设置了门槛,跨过这道门槛对读者来说并不容易。我可以拿博尔赫斯的小说《圆盘》,给“没有反面的正面”一个注解,但接下来由两个清脆的头韵组成的句子(“克雷,克雷基,塞尔特苗裔”),如喷泉跳落三个阶梯,用典同样不易索解。
我赞同T.S.艾略特的说法,诗可以不懂而喜爱。现代派诗歌通常是难解的。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但要适应陌生化的表述。或者说,首先要认同主体对任何一种物化倾向的抵制。
我感到奇怪,周围有些学者、批评家,他们评论木心的作品,恐怕连仔细的观察都谈不上,何以就能轻率地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有的文章自言自语,通篇不见分析,从头骂到脚。恕我直言,除非是门外汉的自信,否则哪来这种自信?
有评论家谈到“肖邦是我的波兰兄弟”这类句子,斥其“空疏、不实”。空疏吗?我倒认为这是想象力的运作,天真而不乏谐趣。
要对木心先生的写作做出评估,评论者恐怕需要多一点积累。本质论、范畴论、方法论等方面的问题,只凭一点想当然的判断恐怕还是解决不了的。要在广博和深邃的程度上去接近这样一个评论对象,我认为还需要努力。
诗人去世已十周年;其写作归属于哪个范畴,迄今尚无定论。换言之,究竟是属于五四文学,还是中国当代文学,还是海外华人文学?好像都是沾边的,但又不完全契合。
这提醒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文脉和语境去考察他的写作,而上文引述的有关现代诗学的“入”和“出”,应该给我们提供一条线索。
“绍兴希腊人”
木心先生的作品,读者只看到两头——初期和晚期,中间阶段是缺失的。童年的几首诗作和晚期的十三卷著作(INK出版社)之外,便是Prison Notes(《狱中手记》)为代表的佚稿,创作于中青年时期,据说数量不少,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没,未见下落。
读者看到的,绝大多数是他移居纽约后的作品。可以说,归在“木心”笔名名下、他认可的创作,主要是一九八二年到二〇〇六年这个时期的产物,他达到了艺术上最终的成熟。诗集《伪所罗门书》是作者在北美大陆制作的最后一部诗集,可视为其晚期风格的代表。
《伪所罗门书》的副标题是“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点明该书的主旨。诗集具有浩瀚的博物志或见闻录的特点;阅读七十四首诗作,宛如穿越一片嗻语的森林。
所谓“个人成长史”,重点不在叙事的对应(幼年成年等分段标志),而在于感悟和决断,针对习常、群集的观念而作的内心顿悟。如:
“如果爱一个世界
就会有写不完的诗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末没有这样的一个世界”
再如:
“去年我是这样过夏天的
伊斯克尔水库,钓鱼,晒太阳
那些都是随俗的借口
无论何方,都可以安顿自己
乡愁,哪个乡值得我犯愁呢”
这种个人化感悟,总是针对“非我”对“自我”的控制和盘踞,直至“自我”终于像是识破骗局,从沉重的纠结中荡涤开来;有时轻逸,有时激烈,有时则苦涩而幽默。
集子里最后一首《山茱萸农场》可视为作者世界观的总结,作为压卷之作是再合适不过了。诗的结尾写道:“虐杀沙皇全家,我未与谋,/尼古拉二世的葬礼,我也不送榇”。将一己的名分从历史中删除,连一个微小的立足点都不占有,“庶几乎形而上上”,终成其纯净广漠、喜剧式的精神之高蹈。
我们看到,无论是历史观、人生观还是宇宙观的表达,诗集都贯穿着一种跳脱、历练、爬罗剔抉的“事后观”,带有木心风格特有的冷娴。
“事后观”的形成是和作者的历史、文化境遇相关。作为象征主义的域外传人,他是时序上的迟到者,也是空间上的局外人。迟到是作者的宿命。然而在主体意识上则别具一种真实,他终究经历了现代诗学的必经之路,并无断裂或毁弃(文稿被抄没也阻碍不了这个精神历程)。他阐释说:
“这个现代精神,首先在于反对浪漫主义,然后经由象征主义的淬炼而凛然脱逸,才取得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大自由。”
艺术上的“入”和“出”的过程由此便清楚地揭示了出来。这个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毋宁说,是体现为精神的某个静止点上的相生相伴,在语言的微观层面达到一种协调和综合。
诗人饶有兴趣地观察(主要是源自欧罗巴的)哲学、伦理、生活方式、宗教、神话等,并且做出回应。一种轻言细语的宏大叙事;写战争、革命、风俗、历史,择其细碎轻小处落笔,以独特的视角(“事后观”)进行观察和评判。迟到者的立场,跳脱者的立场,尼采式的价值重估的立场。一种跨时空的汉语欧罗巴书写。
有些诗作,表达木心作品中常见的浪子主题以及田园风景画主题,如《夏疰》等,笔调尤为轻灵怡人。
“……
又见玫瑰红的光线上下波动
层叠的夏日的疲倦征服了我
情人们将我缠住不放
称我为远归的燕子,鹳鸟
我可并非年年如期赋归的呵
既见,吉祥的是沛泽的肉身
高亢情欲,精练沦浃
夜间我清醒得金刚钻似的”
句法不古不今不中不洋,颇见作者的修辞特性;其语言的掌控称得上是炉火纯青。
《伪所罗门书》是对各种汉语译文的改作。作者毫无违和感地和翻译作品中的人物融为一体,一种纯然是寄生的抒情,而这些来源不同的“素材”经过改造都木心化了。
作者声称:“我是绍兴希腊人。”
这是诗人别具一格的自画像,将其背景和文脉勾勒出来。希腊是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希腊,绍兴是父辈的绍兴,是鲁迅的绍兴;归宗认祖,也是为了继往开来。
他的写作,投入跨国界的“流散”(diaspora)状态,追求汉语语体及言说方式的普世性(cosmopolitan);以现代性为基质而不以现代性为依归,呈现思想的飞翔和综观的姿态,此即所谓的汉语欧罗巴之旅。这个方面他走得很远,走在了地区和时代的局部反应之前。
他的卓尔不凡的诗作,和我看到的任何人的作品都不一样。诗人深知喜剧的深刻不逊于悲剧,以其游戏和象征的超然应对末世论的抗辩。他是独行者,穿行于这个诗歌日益感到陌异的文化语境,描绘出沿途的景观和疆域,给人带来启迪、愉悦和教益。
老少两代闹不好关系,不是年龄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我觉得和青年人很好相处。我懂得他们。青年人,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是艺术家的年龄。热情,爱美,求知,享乐。
——《木心谈木心》
你这样吹过
清凉,柔和
再吹过来的
我知道不是你了
——《五月》
木心生平年表
●1926年3月17日,木心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东栅太平桥畔的孙家老宅。
●1939年,由于乌镇沦陷,日军对校舍进行了破坏,木心在家中学习,开始大量阅读书籍。
●1943年,前往杭州,报考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46年,进入上海美专。
●1948年,被上海美专开除。
●1958年,进入上海美术模型厂工作。
●1979年,担任《美化生活》试刊号主编。
●1982年,前往美国纽约。以“绘画留学生”身份暂住布鲁克林。
●1989年,开始讲授“世界文学史”。
●1995年,回到乌镇。
●2002年,“木心的艺术”巡回展在芝加哥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
●2006年,《哥伦比亚的倒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木心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
●2010年,《木心画集》出版。
●2011年12月21日,病逝于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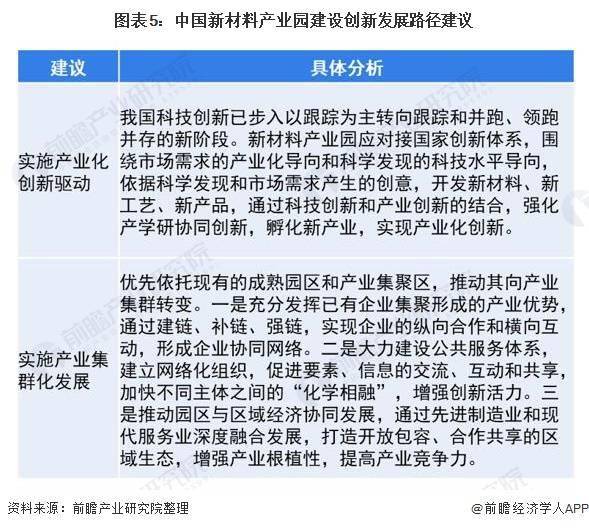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