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代表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读书界形成了一股“丸山热”。《忠诚与反叛》是丸山晚年亲自编订的最后一本论文集,这部论文集讨论了江户幕府体制解体期到明治国家建成为止的日本思想史。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丸山中后期思想的发展。通过阅读丸山对现代性、传统等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百年来所面对的重要问题。
从相信直线式进步史观,转向重视横向的文化影响
读过《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日本的思想》的朋友一定知道,丸山一生的重要思想课题就是日本的现代性问题。这当然是二战对他的巨大冲击导致的。明治维新以来一帆风顺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大日本帝国经历战败这个严峻现实,让丸山等进步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要找出日本之所以误入歧途的原因,丸山的答案就是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上的民主化。他的这种想法其实在早期代表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就有体现。
丸山通过对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如何解体以及对古文辞学派大师荻生徂徕和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研究,探讨江户时代如何从内部产生了现代性的萌芽。虽然他用西学来研究日本思想,寻找日本现代性的做法遭到了包括他的高徒渡边浩在内的一些学者批评――渡边浩说荻生徂徕根本不是什么现代性萌芽的体现者,而是反现代的反动思想家。
但是,他的努力毕竟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他想告诉读者,现代性在日本也有萌芽,并非都是来自西方——这种思路其实在中国学界也不陌生,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因为丸山更多的是从西方思想里吸收思想资源,难免给人以用西方的标准批评日本的感觉。就此而言,有些人说他是“近代主义者”,追求起源于西欧的现代性,并非乱扣帽子。
当然,丸山有丸山的正当理由。想想近代以来,不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曾面临亡国的危险,大量吸收西方文明成了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丸山并非是通常所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当你吸收的外来文化客观上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时,那样的批评就有点苛求了。
不过,丸山的思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大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丸山从相信直线式进步史观的立场,变为更重视横向文化接触,而且也更加主动从本国传统里挖掘更多的思想资源,这在他身后结集出版的讲义录里有很清楚的证据。
这其实跟他本人对吸收外国文化思想的看法有关。他在《思想与政治》(1957)里提到当年流亡日本的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犹太裔弟子卡尔·洛维特对日本文化的一个观察。洛维特说,日本的现代文化好比是一幢两层楼建筑,二楼是西方的,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所有的西方思想应有尽有,但一楼的思考模式却是日本式的。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一楼与二楼之间的梯子却找不到,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无交集,各自成一统。洛维特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没有进入化境,只是停留于模仿。丸山对洛维特的这个批评是大体认同的,所以他在做日本思想史研究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知道了这个思路,我们理解《忠诚与反叛》这本书就容易了。
在思考“忠诚与反叛”中,追问近代日本的命运
在一九六〇年发表的《忠诚与反叛》里,丸山说论文要解决的问题贯穿着三根轴。第一根轴是忠诚与反叛作为思考的范畴或者框架在日本思想史上有何意义和作用。第二根轴是关于忠诚与反叛的对象,就是对谁忠诚,对谁反叛? 第三根轴是探讨用自觉的形式所表明的忠诚与反叛的“哲学”或是“理论”。也许读者会很吃惊,丸山在这里选择的考察对象竟然是很不现代的武士阶层,他讨论武士阶层的忠诚与反叛的关系,跟他一生追求的现代性问题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那他究竟为何要做这样的研究呢?
丸山说日本的“封建的忠诚”的基本模式是基于非合理的主从盟约的团结和“以义而合”的君臣关系联系在一起形成的。在与中国的“忠”这个观念进行对比时,丸山举《困学纪闻》(卷六)里的那句“君之于民亦曰忠,……圣贤言忠,不专于事君”说,中国的“忠”字并不意味着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忠诚。但是这个词在日本的封建主从关系里扎根后,几乎都是表示臣下对君主单方面的献身性奉献——“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始终是支配性的观念。而且与其说是重视合目的性的考量与外在的结果,不如说是以心情的纯粹性作为忠诚的证明,宗教色彩要超过伦理的义务。
在对比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忠诚意识后,丸山说作为战斗者的武士的行为方式本质上是充满力度的,在忠诚的表现方式上有着显著的能动性和随机应变性。所以“臣不可不臣”这个至上命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通过无限的忠诚行动,具有把君主变成真正君主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说,在这种武士的忠诚心态看来,“君不君则去之”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虽然放弃那样的行动原则会产生人格内部的紧张,但也因此反而会让武士面对主君执拗地采取激烈的行动——不是绝对的服从,而是进行谏诤。丸山举了江户时代的山本常朝写武士的名著《叶隐》里对武士绝对忠诚主君的强调,说这并非是对权威的消极恭顺,而是贯穿着非合理的主体性。在丸山看来,正因为有着这种传统,在江户幕府晚期发生动乱和面对国家存亡危机的时候,包括吉田松阴在内的那些武士能够发挥无私的忠诚和主体自律性,具有绝对皈依的感情和强烈的实践性。
丸山在论文中还分析了他的思想英雄福泽谕吉的名分论批判和谋叛论,说福泽对封建忠诚的分解是要进行某种转换,就是把封建忠诚的外面化倾向彻底化,把它提高到公共的水准,从而让私人的―心情的契机能在个人的内部扎根下来。换而言之,福泽是要把非合理的武士魂的能量转化成合理的价值。丸山向来对福泽推崇有加,写过不少关于福泽的文章,有学者甚至戏称他的福泽谕吉研究其实应该冠以“丸山谕吉研究”的名称。在关于忠诚与反叛这个问题上,福泽似乎也是丸山的先驱。
在这篇论文中,丸山还考察了自由民权论中的抵抗与反叛,日本基督教尤其是著名无教会基督徒内村鉴三所遇到的国家忠诚问题、封建忠诚的变质与退化、抵抗的精神与谋叛的哲学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丸山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在论文的末尾,点出了他的意图。他说,随着明治维新的现代化进程,武士存在的土壤消失了,原先的谏诤与谋反这些用词也不符合潮流了。
丸山说他倒不是想发什么思古之幽情,他想问的是:那种原先在日本就很弱的中间势力的自主性,为何在近代日本没有在自发团体里获得创造性转化? 丸山还进一步发问,为何日本近代以来绝对主义式权力集中没有明确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是走向了国家跟社会一体化的方向,这才是跟现代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丸山进一步追问道,近代日本的组织究竟从旧体制的忠诚意识里继承了什么,又舍弃了什么。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现代日本依旧还是个问题,这个“旧债”并没有还清,需要现代日本人通过自己的责任与行动把过去的遗产变为现代的资源。只有这样,“无忠节者亦无叛意”那句话才能超越历史的制约,变成对今人的永恒的预言。
这最后的结语有点不好懂,要联系起丸山的一个主要观点才能完整理解。丸山有个著名的观点,日本近代以来缺乏主体性精神,需要强韧的主体性精神,甚至需要精神贵族主义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主义。因此,他才会从武士的传统里寻找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这是他高度评价武士的谏诤精神的原因所在。丸山评价武士阶层的这种精神品质,当然不是因为他赞美武士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因为如果寻找一种典型的日本人,那就只有武士了。丸山在《忠诚与反叛》的书评会上指出,武士阶层是不存在了,但武士精神还是值得思考的。
探寻日本思想史上的执拗低音,与日本战后启蒙的瓶颈有关
另外一篇长文《历史意识的“古层”》(1972)也是丸山的代表作,是丸山离开东大后不久发表的长篇论文,也应该是丸山著述中引起争论较多的作品。在这篇论文中,丸山想探究的是,日本思想史上是否有某种执拗低音,或者说是原型、古层,在吸收外来思想时会对其做出某种改变。为了避免误解,丸山后来不用“原型”,换成“古层”这个术语。在他看来,虽然这种古层本身没有什么思想,但是总能够对外来的思想文化做出某种改变——这便是丸山的问题意识。他说过要从历史意识、伦理意识、政治意识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看看他是如何在这篇《历史意识的“古层”》里探讨的。
丸山在论文的开头就引用了江户时代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毕生大著《古事记传》里的两段话。第一句是“从古至今,人世间的善恶,以其变化验其来历,均不违神代之趣。后世万代亦可知之”(三之卷),第二句是“凡世间万象,代代时时,吉善凶恶推移之理(中略)悉依神代初始之趣”(七之卷)。本居这样的表述是想说包括未来在内的一切“历史之理”都凝缩在“神代”里了——颇有点像儒家说,最理想的时代是三代。他引用本居的这两句话,想说的是他自己这篇论文的假说,就是本居说的历史的“理”是关于历史性变化的实质内容,如果探讨日本人关于历史的思考与记述的样式,不管是吉善事还是凶恶事,其基础框架就是这句“悉依神代初始之趣”。
丸山接着说他的研究思路,就是从记纪神话,特别是从天地开辟到三贵子诞生的一系列神话找线索,不仅仅当作寻找上古历史意识的素材,而且要从那些思路和记述模式里寻找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历史意识深处执拗地存在的思考框架。研究这个问题时,他采用两部古老的文献,一部是居日本六国史之首的《日本书纪》,另一部则是《古事记》。
丸山在比较了世界上各种神话里关于宇宙生成的模式后,发现其思路里有三个基本动词,一个是创造,一个是生产,再有一个就是生成。在比较了若干用法后,丸山发现通过日本的“古层”看到的宇宙,既非永远不变的事物存在的世界,也非命中注定归于虚无的世界,而是不断生成的世界。这就是第一个基底范畴——生成。
借助对《古事记》的考察,丸山得出第二个基底范畴,就是“次”。因为《古事记》在谈到神世七代的众神出现和制造国土时就是用的这个“次”字,表示一个接着一个的意思。在丸山看来,“生成”以“变迁”的形式发展成固有的历史范畴,而“次”也以“相继”的形式成为另一个固有历史范畴,随着“次”与“相继”向历史范畴转变,象征着两者之间的亲和性的就是血统连续的增殖过程。
丸山接着指出了第三个基底范畴,就是“势”。这也是通过对《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的一些词的用法考察得出的结论。丸山说这两本经典的编者虽然受到中国古代观念的压倒性影响,但同时敏锐地嗅出了跟日本古代传承之间的某种差异性。丸山分析道,“天地初发之时”里所包含的象征性意味已经远远超出《古事记》开头一节的范围,暗示着整个神代史的主题,事实上在日本的历史意识中,跟先前提到的两个范畴一起,形成了一种历史机会主义的原点。具体地说,跟“现在”为中心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后,成为一个新变迁的出发点的现在(生➡现),是一个带有不可测的巨大能量的“天地初发”的场所,具有每一次都补充面向未来的行动能量的可能性。
丸山在论文末尾把上述三个基底范畴用一句话概括出来,那就是“相继生成之势”。丸山说他并不是要用这些范畴简化日本历史意识的复杂多样性,其实这些范畴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没有构成历史思考的主旋律。主旋律在古代是中国传过来的儒释道,明治以后则是西方输入的各种思想。但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范畴会对外来思想进行微妙的调节和修饰,几乎是在意识不到的情形下把整个旋律变成日本式的,发挥着执拗低音的作用。具体说来,比如在江户时代的历史变化中,不是只有现代化的单声道,而且是有现代化跟古层隆起的相克与相生的过程。当然,这样的古层与外来思想的相克相生不仅仅局限于江户时代。
丸山最后总结道,日本历史意识的古层里占据着永恒者位置的是系谱连续上的无穷性,那里构成日本式“永远的现在”。他感慨在失去了约束人们的行动和社会关系的“道理的感觉”后,日本原先就有适宜于历史相对主义泛滥的土壤,很容易变成“趋势”的流动性和相继推移造成的深不见底的泥沼。丸山在这里点出了他研究古层的意图,那就是找出阻碍超越性和普遍性原理在日本扎根的因素。据笔者推测,这样的思路应该跟丸山在一九六〇年代后期的一种挫折感有关。
丸山的一位学生在回忆一九六七年给老师当助教的时候,有次吃完饭一起散步,丸山对他说自己已经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才好了——这位弟子说听了大吃一惊。这真是一个珍贵的记录,以当年丸山在日本学界思想界的地位,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可以遥想丸山当时的心境,也就是战后日本的启蒙遇到了瓶颈。
上至政府下至普通国民,举国上下都追求经济发展,对启蒙这些都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丸山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当然会觉得似乎没有用武之地。可是早先的那些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不时还会重新浮出水面。比如,丸山在战后发表的那篇名文《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中批评的无责任体系问题,在发生重大事件时都会被人提起,说丸山指出的问题并没有消失。如今“无责任体系”已经成了分析日本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发明这个概念的丸山虽然有点绝望,但并没有停止探索,他想找出日本思想传统里的问题,这应该就是他探索古层的真实意图所在。
归根结蒂,丸山是要寻找问题之所在。一九八二年在给《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英译本所写的著者序言里,丸山说自己对日本社会的分析更倾向于病理学的手法,他说自己是十八世纪启蒙精神的追随者,依然固守人类进步这个“陈腐”的理念。他认为“历史是向着自由意识的进步”这句话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精髓。我想,这样的夫子自道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丸山的思路。即便“上帝死了”,以色列没有王了,并非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世界里。
《历史意识的“古层”》这篇论文发表后,至今已有很多学者提出过批评的意见。有的说丸山的论文充满宿命论的调子,也有的说日本根本不存在那样的古层。有人问过丸山是否受到过分析心理学大师荣格的影响,丸山说写作时并没有读过。不过他的好友日本古史名家石田母正则说,很多研究日本史的人都有那样的感觉,认为存在着古层,当然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赞同了丸山的分析。另外一些学者则对丸山使用的文献和他的理解提出了异议。
笔者觉得丸山本来也不是提出一个定论,而是他对整个日本思想史提出了一个解释,想弄清为何包括自由民主在内的外来思想进入日本以后会出现某种变化,是否存在一种执拗低音把外来思想日本化。我想,这是因为丸山在战后的启蒙实践中遇到了某种挫折,才有了那样的问题意识。丸山说写论文时受到自己的经验、自己生活的时代和自己从时代获得的直观感受很大影响。从问题意识的角度来说,他是最敏锐的学者之一,他能够准确地捕捉时代的问题,并提出具有深刻洞见的解释。
至于文献的选择与对文献的解释,当然有商榷的余地,并非定论。就像李泽厚曾经提出过“积淀说”,作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假说,自有其意义,因为我们的确感觉到某种不变的东西的存在。当然,丸山绝不是什么宿命论者,他想通过对日本历史意识的深刻剖析,找出一条克服障碍的路,避免未来某个时刻再次成为某种传统的牺牲品,这就是他的良苦用心了。
绝非简单一句“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家”可以概括丸山真男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丸山绝非简单地用一句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家就可以概括。如果说早期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在战后的一系列实践与思考中,他的立场逐步发生微妙变化,在思考传统与现代化时跳出了原先的直线式进步史观,更加重视文化交流等横向的影响,并且积极挖掘日本传统里的积极因素。可以说,他身体力行了一种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丸山的研究,既有对西学的大量吸收——这点当年跟丸山见过面的李泽厚也很佩服——也有对日本传统的精深研究,两者达到了相辅相成的圆融境界。
在罗伯特·贝拉的那篇演讲里,他提到丸山跟哈贝马斯在论述现代性时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的不同。他说哈贝马斯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利用,而丸山只能依靠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等少数先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一场艰辛的探索。
不过,丸山本人其实并没有抱怨过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不如人。他说过,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是康德和马克思,他不仅吸收了大量西方思想家的成果——比如他从大学时就开始阅读卡尔·施米特的著作,是日本对施米特理解最深和运用最有成就的思想家之一,而且丸山对中国古典文化造诣也颇深。他多次说过要打破地域的局限,他举例说基督教不是欧洲原产的,不是也变成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吗?
所以在取舍之间,重要的是主体的决断。丸山跟很多国际学术思想大师都是好友,除了贝拉外,像以赛亚·伯林、列维-施特劳斯、福柯等都有交往。很多外国学者访问日本时都愿意找丸山交流,因为他既了解日本和东方的思想传统,同时又熟悉西方的理论,能够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阐述日本的思想文化。
这本《忠诚与反叛》出版四年后,丸山离开了人世。在东京千驮谷举办的追思会参加的人数众多,日本学界思想界很多名流都出席给战后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送行。
那时《丸山真男集》已经开始出版,很快讲义录、座谈集和书信集也跟着开始发行,身后出版的著作群也蔚为大观,研究丸山的论文和著作更是从未中断,收藏丸山藏书和资料的东京女子大学还设立了丸山文库和研究中心,这些都显示了丸山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如果要了解战后日本的思想,丸山绝对是绕不过去的一位巨人。《忠诚与反叛》则是了解他成熟期思想不可忽视的重要著作,对我们思考传统与现代性等问题肯定会有不少启迪。
关键词: 丸山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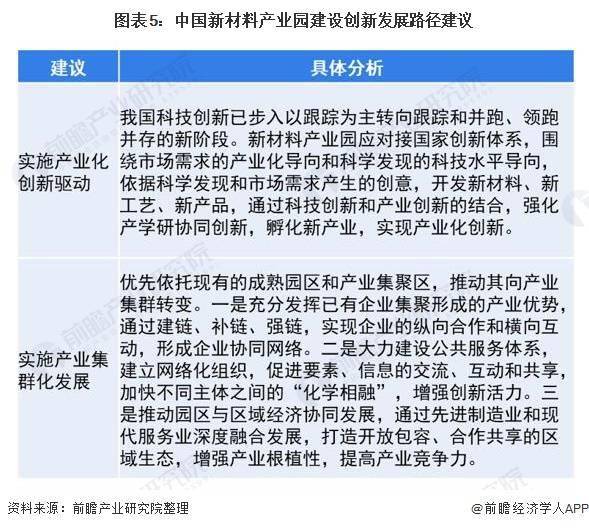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