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明晃晃挂在天上,照得每一处都亮亮的。天气真好,适合看一场展览——我陷在深圳酒店大堂的沙发中愣愣地想。筹备了大半年的“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展”深圳站如期“见人”,喜悦、兴奋、疲惫、怀念交织在一起,让我有一种不真实感。
自打作家汪曾祺同志1997年“不负责任”地“升仙”去了,时间已经又过去了两轮。
老头儿晚年曾有愿望:办一个画展,出一本画集。2020年是老头儿诞辰百年,家里人商量,不如就替老头儿圆个梦,给他在美术馆里正经办个展,于是就有了从去年开始的“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展”巡展。因为疫情,深圳这站的展览拖到了2021年,但所幸,展览顺利举行且圆满落幕。
老头儿曾经写过一首有关“作家画”的小诗:
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
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君若亦喜欢,携归尽一樽。
老头儿是很爱画画的。“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从荷花到人物,他都画。在我的记忆里,他的书房永远飘着“臭”墨味。我曾对此提过意见,被他忿忿地批评“不识货”。据说老头儿作画必须有酒。这个我印象倒是不深——因为老头儿自己仿佛就是酒曲捏的,行动间能自毛孔中散发出阵阵酒香。
除了画画,老头儿也爱读书论、画论。
前几年高邮筹办汪曾祺纪念馆,需要一批老头儿用过的物件。于是全家出动,在旧居中找寻最能“代表”老头儿的遗物。我从老书房里整理出许多画集、画论,还有一堆文房四宝。画论中,涉及扬州八怪、八大山人和徐渭的尤其多。
现今,“随和”“躺平”是贴在老头儿身上的标签,但喜欢八大山人、徐渭的人,怎么可能如此纯粹?徐渭狂纵难驯,八大孤傲落寞。在老头儿随和的外表之下,骨中暗藏狂野透脱。他的书柜里也有宋人花鸟、竹内栖凤,画里的雀鸟毛茸茸的,圆润可喜。但老头儿笔下的鱼鸟鼠猫却都含胸驼背、抻脖背手,像是他自己的自画像;翻着白眼、倔头倔脑的叛逆愤青样儿大概是老头儿对这个世界中看不惯的事情采取的“非暴力不合作”——任你怎样,我若不合作,你能奈我如何?
大概是家里人都没有把老头儿的画当回事,他就特别重视来求画的知音。画得最好的作品,大概永远是他送给别人的那一幅。虽也说“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但他却一次次地把“君若亦喜欢,携归尽一樽”展现得淋漓尽致。印象极深的一次,我眼见得他铺纸、构思、打稿,绘成一幅妙不可言的“麻雀开会图”。画中的麻雀们难得作“正经”姿态,凑作一堆,凝神“开会”。我爱不释手,自告奋勇抱着画,随家人送去琉璃厂的“大千画廊”装裱。从“开会图”自画廊取回,就一直惦记,但一周后再去,画不见了!我翻遍老头儿的书房也没找到“小麻雀”,为此难过了很久。多年后才得知,第二天我的“小麻雀们”就被送了人。如今我还能大致回忆出那幅画的构图,只是不知画在何方。
高考,我考入了前身为国立艺专的中国美术学院,这是老头儿当年在昆明试图投考的备选学校之一。我自认在绘画学问上比老头儿强了一截,大一学了点艺术理论,放假回家看到老头儿的画横竖不顺眼——跟老师说的“好画”完全不一样,横不平、竖不直、气不顺,手腕也没劲儿!一度很是嫌弃。而在为“汪曾祺书画艺术作品展”选画时,突然明白,这大概就是文人画所谓的“雅拙”。
“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老头儿说,“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他似乎对没有成为一个画家深感遗憾,自认为“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单论技巧,他当然是比不得专业画家,但看气韵,却另有一份独有的自在荡在画中,形散神不散。他的书画风格和他文字气息相通,不古不今、亦雅亦俗,随性里带一点俏皮,拙趣中又蕴含着意境。
整理老头儿的书画作品,还有一个发现。他喜欢在画中题上自己文章中的句子——简直就是暗搓搓为自己的文章配图!他在《两栖杂述》里剖白:“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大概这些画就是老头儿写文章时的胸中画意了吧。虽然我已经失去了和老头儿当面“论道”的机会,但是文章和书画对照来读,却似乎是在和老头儿隔空聊天,就像小时候那样,他笑呵呵地评论文章,点拨书画,偶尔撇嘴笑话他人的低级错误。
我在策划展览时,以老头儿的文学作品内容、人生经历为明暗线,把他的文与画结合起来呈现,可以看做我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地发现他的各个侧面、不断重识他的一次“阶段性成果汇报”。把他的“自娱”成果倒腾出来小规模地展示一下,是希望更多的人在感受老头儿“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之余,发现这位饱含温情与狡黠的“文人书画家”。
爱画画的老头儿还是那个老头儿,墨色循心,随遇而安;文画互渗,平易近人。
不要被他“不足观”的自谦骗了。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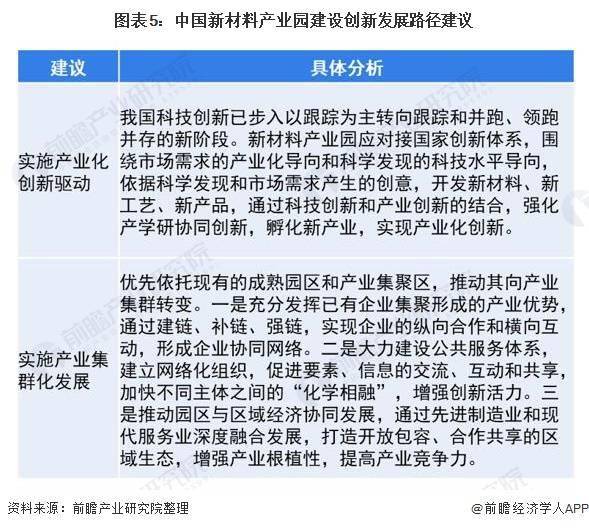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