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芬兰电影周”,此次活动中关注度较高的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阿基是芬兰重要的导演,1957年出生于芬兰的奥里马蒂拉。他年轻时做过洗碗工、垃圾工、邮差和影评家等20多种工作,24岁时为哥哥米卡·考里斯马基写了人生第一个电影剧本《撒谎者》(1981),从此开启了电影之路。后来又同哥哥成立了制片及发行公司。作为高产的电影人,从1980年代开始,兄弟二人制作的影片数量就达到了芬兰全国的五分之一。阿基1983年导演了处女作《罪与罚》后,又导演了“劳工三部曲”“芬兰三部曲”及正在完成中的“欧洲港口城市三部曲”等二十部影片。他的电影深切关注当下社会中的平凡者、失败者和社会问题,对社会体系进行整体性的反思与批判。阿基的电影因其辨识度较高,吸引了世界众多影人和观众,大部分影片获得了国际奖项。他的电影既传统又现代,既冷峻又温暖,既深刻尖锐又充满了爱。
俳句式对白、去表情化表演与抽象主义风格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在创作手法上吸收了默片时代的简约、小津安二郎与吉姆·贾木许等人的幽默与深邃。阿基的电影作品有个分水岭——21世纪之前与21世纪之后。他2000年之前的作品思考深邃,带有浓郁的文人知识分子气息,常常通过简单质朴的故事讲述较为深奥的思想;21世纪之后的作品与吉姆·贾木许《鬼狗杀手》(1999)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阿基后期的电影更多地呈现了形式上的特立独行,如通过俳句式的台词,让表情木讷的角色处于留白的空间之中,展现他们的独立以及最后主体性的建构。影片中,演员按照阿基的规定动作进行表演,表情木讷近似行为艺术式的表演产生了黑色幽默的效果。另外,阿基的夫人是一位现代主义画家,她对他的电影创作影响也较为明显,他很多电影中的美术及造型方面都有架上绘画、现代装置或观念艺术的影子。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爱好者,阿基在早期的《罪与罚》(1983)中,综合了拉斯科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与默尔索(加缪小说《局外人》中的人物)两个人的特质,将他们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建构了电影主人公拉依肯的形象,充满现代意识和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电影中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拉斯科尔尼科夫对“罪”与“罚”的纠结,而在于对整套后人类操控体系的认知与质疑。而拉依肯对这种质疑采取了“局外人”默尔索或西西弗斯式的冷静直面,他的这种方式也影响与提高了女主角的认知。
进入21世纪之后,阿基的电影继续对后人类时期体系操控的反讽,但这一时期的作品少了愤世嫉俗的色彩,多了些宽容与从容。如《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中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沉默式的反抗,影片对法律体系、医疗体系及银行体系等的荒诞性进行了呈现,通过主人公反抗或超出常理的行动,彰显人的体面与尊严。阿基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台词、人物表演及行动较之前的特征更加明显与固定了。台词是诗歌或俳句般简洁的语言,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有某种逃逸线存在,切断了日常人们早已习惯的话语逻辑,新的意义及语境由此产生陌生化效果。电影中的角色表演去表情化,没有丰富的喜怒哀乐形于色,在极简主义的表情下,反而充盈了无限的想象与内容;电影中人物的动作具有行为艺术式的表演特征,是充满疏离感和去个性化的,渐渐带出了普遍性、多样性与自由的特征。
失败者或“废物”们扭转乾坤
阿基·考里斯马基认为做导演必备的素质是真诚,导演的工作应该是“更愿意使一个观众对我的电影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让两百万人留下肤浅的印象”。他的电影不会像商业片那样,要去满足或讨好大众的口味,他以自己独特的作者方式讲故事,告诉观众自己的态度,尽可能地提高人们的认知,这样就会带来一定的不理解与误解。如有人批评阿基在电影中以夸大芬兰贫穷或不光鲜的一面来博取世界的关注,但纵观阿基的所有影片,就会发现他的本意并非如此。阿基的大部分影片都在探讨社会问题,且更在意针对问题如何给出可解决之道。从1983年的《罪与罚》到2017年的《希望的另一面》,从勇敢地直面荒诞到不要失去“希望”,从物质生活方面到精神生活方面,他都给出了一系列建设性与可行性的建议。电影《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通过一个婚姻挫败、因病痛失去记忆的男人重新建构自我的经历,为那些暂时陷入迷失和困顿的流浪汉、蓝领阶层和普通人,建设性地提供了参照与范式。为了避免陈腐的说教与道貌岸然,他在创作上使用了类型杂糅的方式,将黑色电影、公路片、摇滚电影与爱情电影杂糅在一起,充满了独特性:在电影中他既呈现了芬兰当代社会冰冷与贫困的一面,又书写了主人公们英雄式的内在气质——尊严、体面、温暖与自信。
出于真诚,阿基说“他不会拍好莱坞每天都在制造的那种垃圾”,他不会给大众制造一个虚假与虚荣的梦。阿基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平凡单调的人或失败者,甚至那些被叫做“废物”的人,在简单的空间里,在这些人冷峻的沉默寡言中揭示他们的智慧、崇高与英雄特质,最后呈现他们的行动与改变。“人们在其所出生的世界上努力生存”,电影《火柴厂女工》(1990)中的艾丽丝和我们一样,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认真劳动,休闲之余她也追求美好的东西——阅读、追随美与浪漫的爱。她是一个真实而略带腼腆的姑娘,但当她对真善美的追求遭遇了现实的冷漠、伤害与践踏时,艾丽丝开始思考,并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与行动——从“被凌辱者与被伤害者”,到行使猛兽般的破坏力,由此揭示社会与人性的暗昧,呼吁解救之道。
反讽表征下的关爱
阿基·考里斯马基不是一个宅居于书斋的导演。早年间的劳作经历,使身为电影导演的他行走在芬兰的工业港口、低价公寓、集装箱住宅贫民区之间,为流浪者、贫困者、疾病者与生活迷茫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帮助他们找回人的尊严、体面、自信与主体性,并唤起人的崇高之情——这些是带有浓郁芬兰味儿的阿基式电影的主旨。电影《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1989)对物质、消费与娱乐进行了反讽:一个叫“列宁格勒牛仔”的芬兰乐队为了自身发展,盲目地来到美国——他们代表了一部分芬兰人或者北欧人对美国物质诱惑的盲目认知、想象与冲动,他们简单地以为“生活在别处”,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别处”亦如此,遂在虚无与行进中抛掉自我,同美国人或美国酒吧的摇滚乐一起“娱乐至死”,失望的乐队组织者最终自行遁失,不知所踪。这是一个带有隐喻特征的结尾,也预示着娱乐行为、商业消费吞噬着人的存在,导致意义消失。
《爱是生死相许》(1999)也有着如此的反讽与认知:玛利亚和尤哈本来简单而纯朴地过着幸福生活,但开着豪车的城里人什米卡出现后,一切发生了变化,他为玛利亚带来外面物质世界的诱惑——时尚杂志、速成食品、化妆品、服饰等,华丽的东西打破了玛利亚的幸福生活,使她走向复杂而痛苦的“现代生活”。玛利亚被什米卡引诱后离家出走,在城市里服务于金钱与男性统治,坠入什米卡所谓的“没有痛苦,我都活不下去”的现代主义陷阱,陷入颓废与媚俗的不幸福之中。两部影片通过对比的手法,凸显了淳朴生活的重要意义。
电影《希望的另一面》中,工作了一辈子即将退休的女售货员对男主人公维克斯特伦说“下个圣诞节我要去墨西哥,喝喝清酒,跳跳舞,清静了这么久,我得活动活动”,这是对“工作”这个操控系统的反讽与应对——当我们获得工作时,以为获得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但是这是虚假的“自由”,它附属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与运行体系,人只是其体系上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脱离体系考量的话,无从谈“自由”。
《薄暮之光》(2004)中的科因斯泰恩被同事排挤,在监狱中,他和狱友打成一片,有说有笑。当烤肠店女孩找到他,他说自己要开个机修厂,虽然被同事、银行信贷部经理及黑社会老板的女友称为“废物”酒吧,他还是有希望,而烤肠店女孩也很高兴看到他没有失去希望。这就是阿基给跌入谷底的人的一个启示:无论如何都不要失去希望。黑人小男孩一直凝视着他。影片结尾处,小男孩拉着被光头纳粹虐待的狗,叫烤肠店女孩去救被殴打致伤的科因斯泰恩,践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式的平衡与希望。
局限与挑战
芬兰人喜欢用“sisu”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民族性格,它是“善良诚实、遵纪守法、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以及坚韧顽强的精神和异乎寻常的耐性”的意思,这些特征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人物身上悉数出现。阿基26岁自编自导处女作《罪与罚》时,就站在了文学巨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家小津安二郎及哲学家加缪的肩膀上,结合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与北欧的宗教存在主义认知,对存在、信念与社会体系的现代性进行思考,以严肃的思考、幽默的反讽与人道主义关怀,对工业化以来的芬兰或人类的普遍性特质进行书写,含蓄但不失犀利,冷峻但不失温暖,反讽但不失关爱。
考里斯马基的电影有着自己的个性与可辨识度,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在叙事形式、主题立意与建构人物的方式等方面,有自我重复之嫌。例如,电影《勒阿弗尔》(2011)与《希望的另一面》是两部关于难民的电影——难民问题复杂而尖锐,但阿基依旧运用他一贯的浪漫、温情与“悲悯者”形象等手法来讨论这一问题,其形象与立意过于乌托邦化或理想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问题的严肃性和思想的深刻性。阿基的“欧洲港口城市三部曲”还未完成,期待下一部作品中,他能超越自己。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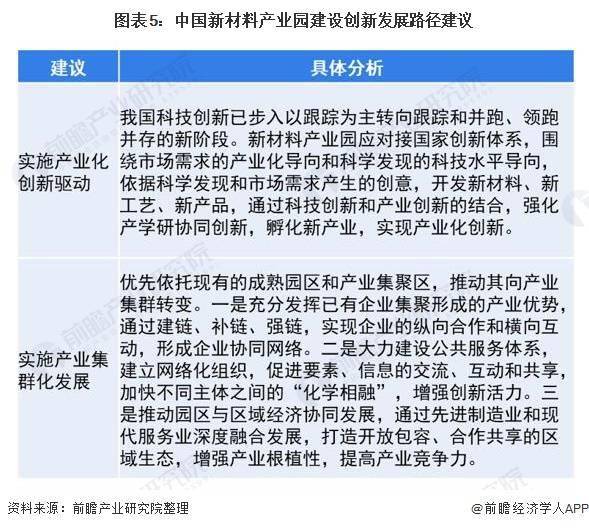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