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绎任何一首歌曲时,黄贯中都会将自己的热情释放到舞台上。他无法形容那种感受是怎样的,只知道自己能把灵魂交给他最爱、最相信的音乐,“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是活着的”。
这么多年,黄贯中从来没变过,始终真挚热爱着他喜欢的一切,无论有多少诋毁和谩骂,他都坦然接受。Beyond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盔甲。
这次面对面的采访,发生于《披荆斩棘的哥哥》滚烫唱演家族诞生之夜的前一晚,虽然连日来忙于紧张和密集的训练,但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儿疲惫与倦怠。他说话气息朴素,时不时以一身“前辈范儿”,讲讲大道理;但他似乎又是最没有“前辈范儿”的人,没有脚不着地的片儿汤话,大多表达都融入了多年的生活阅历。聊到彼此认同的话题时,还会不自觉地拍起手来,兀自笑着。
在黄贯中的人生中,有很多沉默时刻都是因为他那位离去的兄弟——黄家驹。“我就是很想他,很舍不得他。”他说,想向每一位唱过Beyond歌曲的朋友道声谢谢,因为这些朋友,家驹才可以继续存在着,Beyond乐队的精神才可以永存:“你们每唱一首他的歌,都是在延续着他的生命。其实他没有走,他一直都在,当音乐响起时,他比任何一刻都贴近我们。他不在天堂,不在地狱,只在我们心里。”
《我是愤怒》
愤怒这种情绪,不分年龄
在Beyond的众多经典作品中,黄贯中认为,只有《我是愤怒》最能代表他。
这首歌曲收录在Beyond四子推出的最后一张大碟《乐与怒》中。专辑里,黄家驹作词作曲的《海阔天空》成为传世经典,而由黄贯中填词的《我是愤怒》虽未能成为大热门,却也承载了他在音乐创作、为人处世上的铿锵心声。两个人,一个人高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一个抱着吉他宣泄“真本性,怎可以改”,铸就了Beyond乐队的光辉岁月。
“《我是愤怒》很简单、很直接,但愤怒并不单单是情绪表达,是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会有所反应,要讲出来、要申诉,是种正义感,一种做人的坚守。”说这话时,黄贯中略带激动,“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愤怒,你还年轻吗?可我觉得,这种情绪不分年龄,看不过去的,就要说出来,包括在音乐上,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他一向坦率,喜欢有话直说:“我没有什么好躲好藏的,你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我也没办法。”
可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黄贯中却不再是那个“又酷又拽”的乐坛前辈:跟大家打招呼时,他总是习惯性地俯身、鞠躬;听别人讲话时,也是全神贯注。观众甚至形容他温柔得像“妈妈”,这让他有点儿抓狂,“这可太不摇滚了”。
黄贯中说,《披荆斩棘的哥哥》之所以找他,大概因为他根本没有综艺感,也绝对不是综艺人,不搞笑,全身“产不出梗”,也不擅长矫揉造作地作秀。但他还是答应了,因为节目能给他极大的创作自由,没有台本,却能挖掘人性。还因此见识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他可以和这么多人住在一间房里,从早上八点对着他们到深夜;可以和这些不同性格、不同领域的人融合;他发现,自己还能打鼓、跳舞,尽管跳得“拙劣”,但他是可以跳的。
至此,黄贯中欣然地接受了自己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的一切改变,他从心底里满意,虽然有些时候拼命训练真的很累,“我不是说一定要去争取掌声、人气和观众的喜爱,这些都太抽象了。其实能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足够了。”
《光辉岁月》
录音、拍戏连轴转,但愿为兄弟妥协
“想开点,看开点”,这个道理黄贯中一直都懂,只是年轻时想不开的时候实在太多,让他来不及思考。
1985年,那是Beyond成立的第三个年头,一群热爱音乐的摇滚小子为参加比赛组成地下乐队。想办演唱会却没资金,叶世荣邀请正在设计系念书的好友黄贯中帮忙设计海报。谁料到,演唱会开始前,吉他手突然提出要离开,会弹吉他的黄贯中被拉去救场,做顶替,“这一顶,就顶了二十多年”。因为种种偶然,Beyond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连黄贯中自己都感叹,有时不得不信服命运的安排。
顶替前,黄贯中有自己合作的乐队,再加上一个月要学三十多首歌,Beyond的作品近乎原创,难度极高,还要登台,空闲时间还得做海报设计,他问“怎么可能?”但黄家驹说:“不要紧,我有信心的,你可以做到。”事已至此,“唱吧!”黄贯中作为Beyond成员的首次登台完全被紧张笼罩,他顾不上炫技,用全场最让人惊艳的长发遮住大半张脸,埋着头一直弹一直弹,连一旁的黄家驹见状都忍不住喊:“你像个木头桩子,就不能动一下吗?”黄贯中回应:“我一直在动啊。”直到看回放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整个人都僵在那里:“我如今再看过去的造型和表现,都会想‘你在干吗’。不过,那时候的长发、夸张前卫的配饰,真的挺大胆的,我很欣慰当时够胆去尝试这些新东西。”
Beyond的成长从来都不算顺利,但“够胆”伴他们闯荡多年。从地下乐队唱到地上,出了唱片却屡遭失败,音乐风格遭遇抨击。更难受的是那几年的黄贯中,他回忆,“为什么这么变态啊!我都要吐血了”。彼时,Beyond不仅要工作挣钱,还要贴钱出碟、办演唱会,黄贯中不得不连轴转:一边在设计公司工作,一边和乐队演出,最让他崩溃的是还要兼顾拍戏:“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拍(电视剧),半夜丢给我二十多场戏,每场都那么长,每天拍到很晚才收工。那时我每晚都要先去录音棚,录完音队友们可以休息,但我还要去片场拍戏,我觉得不公平,也很愤怒。”他愤愤不平于其他三人可以休息,但支撑他坚持下来的正是这三个人:“他们告诉我要为乐队着想,你拍了电视剧,我们的歌就有可能成为主题歌,这样听我们歌的人就多了。我说,好吧,拍,重要的是把团队搞红。”
那时的黄贯中不够自信,甚至有些木讷,总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所以那段人生中,很多决定都是黄家驹帮他做的。就像有天黄家驹给了他一首歌,“阿Paul,你唱这首歌吧,你比我唱会更好。”看他态度犹豫不决,黄家驹补充一句,“就当是为我们而唱的。”1988年,专辑连续失利的Beyond迎来了事业转折点,由黄贯中主唱的《大地》获得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同时奠定了Beyond在香港乐坛的地位。
“为团队做事”,成为黄贯中多年来的信仰,他说,他容易被这种集体荣誉感所“利用”,为兄弟情义去做妥协。即便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他依然坚定地信奉着没有团队就没有自己:“可能我们所处的圈子是没办法避免比较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人气排名会有先后,但我并不在意,也没什么胜负心。可如果你想让我一起为团队争光,我就认为这事必须要认真,就像那个年代,咬牙坚持拍戏,是因为觉得有东西可以交换,我受这个苦但可以给乐队带来想要的东西,想要什么?就是音乐。做好这些,可以继续我对音乐的爱。”
《无悔这一生》
人要是留在回忆里,就只剩后悔了
1988年,黄贯中曾随Beyond来北京开演唱会。开场伊始,在门口徘徊的黄贯中巧遇黄牛,“今晚有个摇滚乐队演出,要票不?”他拿到场外的宣传海报是用笔随便画的,画中人和他们一点儿都不像。围观他们的人也都带着异样的眼光,“他们都不知道Beyond是什么。一开场,还喊着‘这是什么音乐啊,这么吵’,接着就紧紧捂住耳朵。”过了十多年,当他们再来内地时,已全然不同。“中间有十多年我们都没来过,再来就发现,内地的观众都会唱我们的歌,还是用广东话,我很诧异。从没有想过这么多人会喜欢我们的音乐。”
1993年,是诞生经典的一年,同时也是Beyond最黑暗的一年,主唱黄家驹倒在了舞台上,一切都回不去了。
外界铺天盖地地热议着“Beyond失去了主力就此完蛋”,黄贯中也跟着“崩了”,他来不及去想家驹的离开到底意味着什么,乐队会怎样。他只清楚一件事情,“我的兄弟不在了,我接受不了”。对于家驹的离去,黄贯中在内心做了很多假设,他是自责的,后来的两三年,他一直在想,“如果一切没有开始,又何来发生”。他沉默数秒,眼眶却早已泛红,“真的,我一直想,如果我不认识他就好了,要是我没和他玩音乐,没有组成Beyond就好了,起码他不会走;要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成功就好了,就不会被日本公司签约,不去日本发展就不会有那次意外,他就不会……我不想再玩(音乐)了,不想再继续了。”他停了停,“我总是这么想,但现实很残酷,让人很难过。”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黄家驹是最懂黄贯中的人,他们习惯在一起弹吉他,聊音乐,他会慷慨地把自己的音乐给黄贯中演绎,他们更多是一种惺惺相惜的默契。家驹没了,致命的打击让黄贯中极度想和音乐断交。他陷入痛苦和忧郁,这是他坦承过的低潮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抑郁,根本不想玩音乐,生命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直到后来,我才慢慢接受那时候的自己,才发现人要是永远留在回忆里就只剩下后悔了。”转头,黄贯中接下主唱的担子,带着乐队离开日本,履行约定,继续着黄家驹未完成的路。
可惜,他们没能再创曾经的辉煌,2005年,Beyond在世界巡回告别演唱会上正式宣布解散,一代传奇彻底落幕。
《海阔天空》
从不担心,Beyond会被遗忘
音乐到底应该为何而存在?在光怪陆离的当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千百种,每一种选择都会通往不同的方向。但对黄贯中而言,音乐成了他对抗一切不快的武器。
黄家驹走后,剩下的三人每当有乐队表演时,黄贯中依旧站在左边,黄家强在右边,坐在后面的鼓手叶世荣眼前永远是空荡荡的,“难过”,但他们知道这个位置是家驹的,他还在这里。“你会担心Beyond有一天被这一代人遗忘吗?”“我只知道家驹不在了,他想要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做。我也不担心会被遗忘,因为我知道唯一对抗的方法就是好好玩音乐。”
这些年,黄贯中紧紧拽在手里不放的是:信仰。每当Beyond的经典曲目在不同场合响起,他都会抱着吉他,凑向麦克风,发声、动情、歌唱。“为什么每一次都那么投入?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我起码唱过一千次的《海阔天空》,唱不腻,听的人也不会腻。大概因为演唱者和听众是可以通过音乐连在一起的,你们享受,也能触动到我。”黄贯中也分不清这是什么音乐魔力,他只知道这承载了情怀和热血。
这些年,黄贯中的舞台从不缺呼喊,有人说他和家驹的台风、声音越来越像,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起Beyond,怀念那个走了近三十年的人,“我跟他的声音很不同,演绎方法也有区别,但我并不介意别人这样认为。我没办法跟家驹比,他是神一样的存在,但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投放那种感情,因为我们对音乐的心是相同的,所以大家会认为我们散发的能量是一致的。”
除了在舞台上的锱铢必较,生活中他学会放慢节奏,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入行36年,很多事情都不懂的小小吉他手,他会在网上“冲浪”,看到别人把他年轻时的照片和现在进行对比,也会奇怪,“我都57岁了,每天都有人问我怎么防老。我说,做人开心点儿,开怀点儿,不要总去想不好的事情。现在的人日夜辛苦打拼,很容易忧心,担心有没有钱买房、生子,做任何事情都有目的,这样容易老得快,想开点儿,会让人年轻的。”
“有人认为我一心搞摇滚,很笨”
新京报: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发现你是个感性、直接的人,就像你在节目中说的,可能大家以后会忘记彼此。
黄贯中:是的,每个人都爱讲漂亮话,比如会说永远记得对方。但那一刻我真正的想法就是,或许大家会慢慢忘记这一切。因为做这行太忙,忙碌会让人淡忘,可能再碰面连彼此的名字都喊不出来。人就是这样,你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就会淡忘。不过,忘记并不代表感情就结束了。
新京报:不随波逐流且坚持自我,这让你在娱乐圈应该很难吧?
黄贯中:非常难,很多时候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圈子。但一定有人认为你适合,有些事也正因为你不适合,所以你又很适合,这种感觉很“变态”。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把家驹的很多东西保留了下来,坚持他的音乐风格,追求纯粹极致的摇滚。但这始终不是大众认知中的主流音乐。
黄贯中:我喜欢摇滚,都玩一辈子了,就为了迎合市场,放弃自己喜爱的东西,会不会太残忍了?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只有坚定地追求心中所爱,才可以让我活得更扎实。
新京报:当年有没有人劝你换一种更流行的风格,或者去做些更商业、更容易有经济回报的事?
黄贯中:当然有啊!这些人绝对比叫我继续玩摇滚的人多得多。三十年前,我跟李克勤一起拍电视剧,每天都有几拨儿人来劝我“你演戏吧!你会过得很好,会更受欢迎,拍戏的钱很容易就到手,玩什么摇滚音乐啊!”他们认为我一心搞摇滚很笨,是傻瓜、疯子。到了今天,当初劝我放弃摇滚音乐的人在哪儿?他们都不见了。或许他们很有钱,我获得的成功也不是他们认为的成功。可如果将目光都聚焦在钱上,你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需要不断的掌声和名利,好像中毒一样。我不渴望这些东西,那也不是我需要的。
新京报:很多人称Beyond为殿堂级乐队,你们拥有很多骨灰级粉丝,这些追逐从没有改变过你吗?
黄贯中:改变不了,我的努力是为了我喜欢的东西,这绝对是应该的。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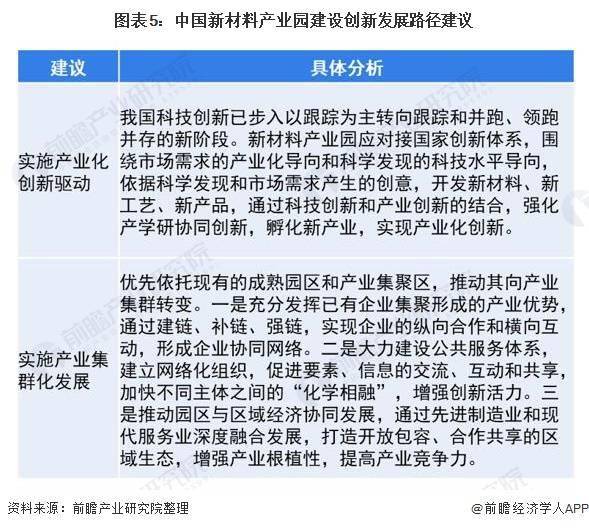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