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在《宏观经济政策评价报告》基础上,进一步构造了潜在增速、产出缺口、潜在增速缺口、货币政策力度指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和政策效率指数等宏观政策指数。宏观政策指数有助于政策界和学术界更理论性地、更系统地了解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
一、潜在增速与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1.潜在增速与产出缺口
潜在增速与产出缺口是分析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核心指标。本报告基于生产函数法测算潜在增速,进而测算产出缺口。2022年中国潜在增速预计为5.4%,新冠肺炎疫情以来2020—2022年中国潜在增速的均值为5.3%,比疫情之前2017—2019年潜在增速的均值下降了1.1个百分点。
2022年一季度的产出缺口为-0.6%,相比2021年全年的产出缺口(-0.2%)有所扩大。负向产出缺口扩大主要与3月份以来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剧等突发因素有关。多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也反映了突发因素的影响: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5%,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回落2.5个和2.9个百分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49.5%,重新跌至荣枯线以下。
从全球范围来看,一季度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下行压力均显著增加。IMF在4月份对全球经济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6%,相比1月份的预测值大幅下调了0.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最新预测值为3.3%,相比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0.6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最新预测值为3.8%,相比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1个百分点。
因此,对于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要客观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疫情加剧等国内外突发因素对中国经济运行带来的新挑战,宏观政策需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经济韧性足”,经济增速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
2.潜在增速缺口
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的视角来看,不仅实际增速会偏离潜在增速进而形成产出缺口,而且潜在增速也会偏离其本身的合理水平进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是指当经济结构处于最优状态时的潜在增速。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结构黏性以及多种结构失衡之间的嵌套循环,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有可能偏离其合理水平,从而形成潜在增速缺口。如果潜在增速缺口为负,表明结构性问题对潜在增速产生了抑制作用。本报告采用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测算潜在增速缺口。
本报告基于2022年一季度的最新数据测算得到,2022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缺口预计为-0.14%,低于2021年的-0.12%,也显著低于疫情之前(2017—2019年)的水平。究其原因,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有所加剧,尤其表现在供给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两方面。就供给结构而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再加上国内多地疫情加剧,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堵点,从而加剧了供给结构失衡问题。就收入分配结构而言,疫情影响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持续低于平均值增速,表明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这些结构性问题使得潜在增速的实际水平相对于其合理水平出现偏离,最终导致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有所扩大。下一步,宏观政策需要加强对结构政策的运用,着力优化供给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多方面经济结构,更好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尽快推动潜在增速向其合理水平靠拢。
二、宏观政策力度指数
1.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力度的大小。本报告计算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性指标和逆周期指标。政策工具性指标直观反映各类政策工具的力度,包括M2同比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等数量型指标,以及DR007和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实际利率等价格型指标,共计4个指标。逆周期指标旨在体现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本质,包括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以及DR007等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共计4个指标。将上述8个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即可得到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2022年一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为45.4,与2021年全年相比小幅升高0.3。需要注意的是,在与2021年进行对比时,应该剔除疫情给2021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带来的基数效应,否则将会高估2022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的涨幅。测算结果显示,如果不剔除疫情带来的基数效应,2021年全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为43.0,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全年相比大幅提高2.4;剔除疫情带来的基数效应之后,2021年全年货币政策力度指数调整为45.1,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全年相比小幅升高0.3。
一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的上升,是由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共同发力所促成的。就价格型货币政策而言,央行在2022年1月17日将1年期MLF中标利率和7天逆回购利率降低10个基点,这是2020年4月之后时隔近两年时间央行再度启动降息操作,降息带动市场利率下行。货币市场利率DR007在2021年的均值为2.168%,2022年一季度均值则下降到2.095%。货币市场利率的下降也进一步带动了信贷市场利率的下降。就数量型货币政策而言,虽然2022年一季度没有降准,但是央行加快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也起到了释放基础货币的作用。3月末的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速分别达到了9.7%和10.6%,与2021年末的9%和10.3%相比双双升高。
虽然一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小幅升高,但是中国经济产出缺口却从2021年的-0.2%扩大至2022年一季度的-0.6%,可见下一步货币政策力度有待适度增加。一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有所不足主要是受到潜在通胀压力和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加息周期的掣肘。不过,从最新政策动态和走向来看,3月末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已经明确要“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而且,央行已经决定“于2022年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为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力度,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可以预见,二季度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将进一步提升,从而“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2.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财政政策力度的大小。计算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指标体系同样包括政策工具性指标和逆周期指标。就政策工具性指标而言,主要包括财政支出增速和财政支出进度等支出端指标,财政收入增速和宏观税负等收入端指标,以及不同口径的赤字率指标,共计10个指标。就逆周期指标而言,主要包括两个口径的财政支出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以及两个口径的财政收入对经济运行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共计4个指标。将上述14个指标进行指数化处理,即可得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2022年一季度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为50.9,与2021年全年相比小幅升高0.3。与货币政策力度指数类似,需要剔除疫情给2021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带来的基数效应,否则将会高估2022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涨幅。测算结果显示,如果不剔除疫情带来的基数效应,2021年全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为48.6,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全年相比大幅提高2.3;剔除疫情带来的基数效应之后,2021年全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调整为50.6,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全年相比小幅升高0.3。
一季度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上升,主要是由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速提升和支出进度加快促成的。就财政支出增速而言,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速达到了8.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政府性基金支出之和的同比增速更是达到了16.2%,这两个指标在2021年全年分别仅为0.3%和-1%。就财政支出进度而言,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执行进度达到23.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政府性基金支出之和的执行进度达到了21.8%,分别比2021年同期高出了0.3个和1.8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速和支出进度的加快,带动赤字率上升,一季度宽口径赤字率(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口径)达到了4.6%,大幅高于2021年同期(0.1%)。不过,一季度非税收入同比增速达到了14.2%,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政策力度指数的涨幅。
考虑到一季度负向产出缺口有所扩大,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通过历史对比可知,疫情之前的2017—2019年产出缺口在-0.1%至0.2%的范围内徘徊,期间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平均值达到了54.5。2022年一季度的产出缺口扩大到-0.6%,财政政策力度指数却显著小于2017—2019年的平均水平,可见一季度财政政策力度的确有待提高。下一步,可以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的执行进度,并且更加有效地落实减税降费举措,从而提高财政政策力度,更好地应对“三重压力”。
三、宏观政策效率指数
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用来综合反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整体调控效率,这是因为现实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相互影响,难以准确剥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调控效率。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GDP/M2增量、GDP/信贷增量、GDP/政府债务增量与GDP/财政支出增量四个子指标构成。子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一单位的货币数量扩张或财政支出规模扩大能够带动的总产出越多,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也就越高。考虑到宏观政策的时滞性,本报告测算的某个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反映的并非是当季度宏观政策所采取调控举措的效率,而是站在当季度的时点上评估一段时期以来的宏观政策效率总体情况。
2022年一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为48.2,比2021年四季度下降1.5。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下降主要是与货币政策效率相关的子指标下降有关。GDP/M2增量从2021年四季度的1.04降至2022年一季度的0.98。相比之下,与财政政策效率相关的子指标中,GDP/财政支出增量从2021年四季度的0.79微升至2022年一季度的0.80,GDP/政府债务增量与2021年四季度基本持平。
客观上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一直没有恢复至疫情前2018—2019年的水平。主要原因在于,疫情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供给结构失衡与收入分配不均衡等结构性问题有所加剧。这使得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一定阻碍,宏观政策难以有效带动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要想进一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需要优化经济结构并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尤其要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三者之间的协调配合,促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
附注:
1.主要指标测算方法与步骤
(1)潜在增速:本报告采取生产函数法测算得到潜在增速。具体而言,首先测算资本存量、实际有效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存量等各生产要素的年度数据,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等时变参数进行估计。结合估计得到的生产函数,计算各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再对资本存量、实际劳动力规模、人力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等各生产要素和估计出的要素弹性数据进行滤波并代入生产函数中,即可得到各年度的潜在产出,进而计算得到各年度的潜在增速。
(2)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等于经济体的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的差值。在计算季度产出缺口时,需要用到季度潜在增速。由于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在短期内较为稳定,因此本报告假设每一年内四个季度的潜在增速是相等的,并且都等于年度的潜在增速。
(3)潜在增速缺口:潜在增速缺口等于潜在增速与潜在产出合理增速的差值。本报告采用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测算得到潜在增速缺口。通过基于经济波动频域识别的BP滤波法对实际产出增长中的超长期、长期、中期与短期部分进行有效估计,由此可以得到潜在产出的长期合理趋势。基于潜在产出水平的长期合理趋势可以计算得到各年度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将其与实际的潜在增速作差,即可得到各年度的潜在增速缺口。关于潜在增速缺口测算的方法和技术细节,可参见:陈彦斌、陈伟泽,《潜在增速缺口与宏观政策目标重构——兼以中国实践评西方主流宏观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2021年第3期。
(4)货币政策力度指数:将M2同比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DR007、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实际利率等4个政策工具性指标,以及M2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DR007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DR007对通货膨胀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等4个逆周期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货币政策力度指数。
(5)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本报告主要从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赤字率的变化来考察财政政策力度的变化,进而构建财政政策力度指数。根据《新预算法》,完整的预算体系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账”,不过社会保险基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规模非常小,因此本报告重点分析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两本账”的财政政策力度。将一般公共预算(窄口径)和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宽口径)两个口径下的财政支出累计同比增速、财政支出执行进度、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宏观税负、赤字率等10个政策工具性指标,以及两个口径下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和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的逆周期调节指标等4个逆周期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财政政策力度指数。
(6)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于现实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传导相互影响,难以准确剥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自的调控效率,本报告采用GDP/M2增量、GDP/信贷增量、GDP/政府债务增量与GDP/财政支出增量等4个子指标计算得到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用来反映宏观政策的整体效率。考虑到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M2、信贷、政府债务与财政支出的增量采取季节调整后的当期及滞后5期(共6期)的累计增量进行测算。由于M2、信贷、政府债务是存量值,所以6期的累计增量是由期末值减去期初值测算得到。由于财政支出本身就是每期的增量值,所以6期的累计增量是将各期财政支出规模加总得到。对4个子指标分别采用Z-Score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不同权重,然后加权平均即可得到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由于宏观政策从出台到发挥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本报告测算的某个季度宏观政策效率指数反映的并非当季度宏观政策的效率,而是站在当季度的时点上评估宏观政策效率的总体情况。
(7)政策工具性指标的规则建议值:本报告基于GMM方法,分别使用泰勒规则、麦卡勒姆规则和财政政策规则,计算得到了几个重要政策工具性指标的规则建议值,包括DR007、M2同比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同比增速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速等指标。在计算过程中,本报告将相应政策指标的滞后一期变量纳入规则方程,使得政策规则更加符合央行和财政部政策操作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政策规则所测算的指标值更好地与现实数据进行拟合。将政策规则建议指标数值与实际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力度变化。
2.相关数据来源说明
计算潜在增速使用的GDP增速、劳动力、人力资本等指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或者根据相关指标计算得到。计算货币政策力度指数使用的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DR007等指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计算财政政策力度指数使用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宏观税负、赤字率等指标来源于财政部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计算宏观政策效率指数使用的政府债务等指标来源于BIS数据库或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的过程中,综合考虑指标数据可得性,将2000—2020年作为基期计算均值和标准差,并且剔除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2009年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2020年数据。此外,为了避免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基数效应,借鉴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等部门的做法,将2021年的潜在增速、GDP增速、M2同比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等指标采取2020年与2021年两年平均值加以替代。
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利率、政府债务率等个别指标的发布存在一定时滞,本报告首先对相关指标进行预测,然后计算得到各个指数。待相关指标正式发布之后,将对相关指数的最终数值予以修正。(陈小亮 刘哲希 陈彦斌)
附表
————————————
作者信息:陈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编审;刘哲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关键词: 宏观政策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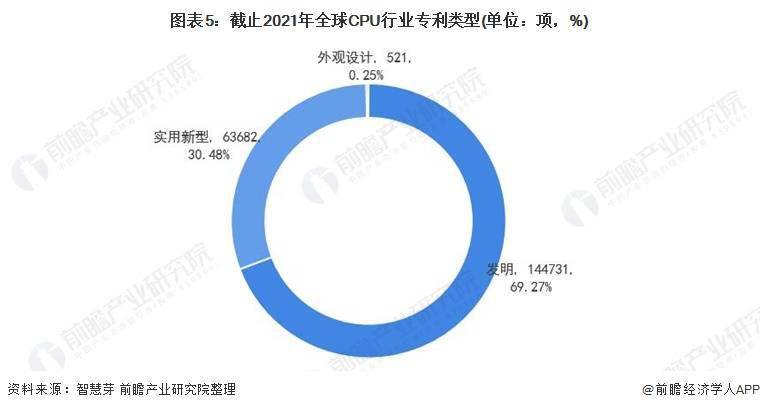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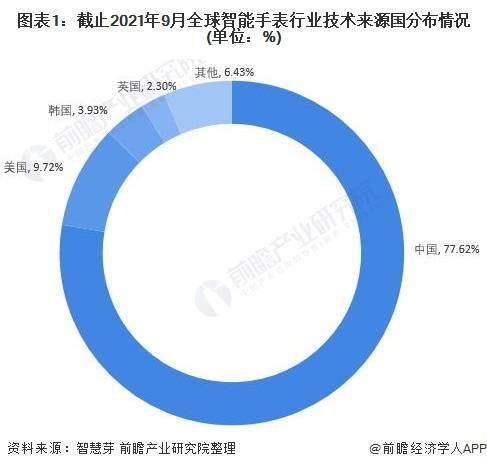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