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启发是,中美货币政策差异主要是由经济金融结构特定决定的,都达到了大致相同的效果。这轮应对全球疫情,中美货币政策在取向、工具选择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两国的经济金融结构差异高度相关。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政府和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货币政策取向与工具的选择中,充分利用了这些结构性特点,借助政府、银行,实现了金融和经济的稳定。美国金融体系以直接融资市场为主,价格工具能发挥更大作用,采取了较大幅度的降息。此外,微观主体的承受能力不同,也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选择。如我国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可以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但美国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较高,储蓄率较低,更多地采取直接救助的方式。
但从最后政策实施的效果看,都实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维持住了经济的必要循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最初是为了防止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提供必要的美元流动性并支撑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市场主体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而后与财政政策形成了紧密配合,将资金输送到企业和消费者手中。在这个特殊时期,需要财政的预算软约束实现货币的创造和投放,双方最后殊途同归。当前,美国又面临以大宗商品价格为主导的价格上涨压力,货币政策表现得较为“宽容”,处于“等待和消化”供给冲击的状态。
第二个是个困惑,中美之间可以容忍多大幅度的货币政策偏离,或者说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长期采取极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中,我国的正常化的货币政策能维持到什么程度?能维持多久?美国既是经济强国,也是金融强国,更是世界货币的主要提供者。美国的经济周期、金融周期和政策选择,必然会对世界经济、金融状态产生根本性影响。在世界经济相互联系、金融有一定连接的情况下,中心国的经济、金融,特别是政策外溢是必然的,对于非中心国家,也许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冲,但只是表现为承担调节成本的主体、环节不同,但冲击都需要承受的。可以加大汇率波动幅度,由跨境主体承担价格波动,提高非贸易品的相对安全性。但资本高度参与的汇率市场,汇率也成为金融资产,价格也存在大起大落的风险。在我国经济规模足够大,仍保留一定的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渠道,汇率更有弹性的情况下,国内货币政策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但影响仍存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影响不同的主体。
第三个是财政和货币的合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在一个货币区内,财政与货币的合作,犹如体外生命维持系统,可以持续不断地维持生命系统的循环,但也带来对这套体外生命维持系统的依赖,形成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很难培育出自我免疫能力和活力,打破自我循环。西方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很难从现在组合里退出来。资产市场的有效运作,将低利率记忆下来并锁定。一定提高利率,政府的债务利息会大幅上升,资产价格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性会受到挑战。资产负债表衰退,既在衰退期发挥作用,在利润改善时也出于改善资产负债表压力,无力推动新资产的扩张。为稳住资产负债表的政策措施,将资产负债表锁定在特定利率水平上。既缺乏动力,也缺乏条件,走出舒适区。
我国也在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一方面,从我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经济处于旧结构坍塌,新结构孕育的阶段,政策上既需要“看见”未来,又需要“熬过”当下。在某种程度上,“剩者为王”,强调“跨周期”宏观调控。这需要充分借助周期以外的力量,主要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政府部分将财政和货币连接起来,可以延长特殊时期的经济“耐受力”。因此,我国既需要增强政府支持经济的能力,也需要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实际上,在高质量增长要求下,政策性金融缺口是现实存在的。这个缺口的弥补,或者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弥补,或者通过财政赤字的金融化甚至货币化强制弥补,或者通过政策性金融方式实现。我们有必要测算这三种方式的利弊得失,作出科学的选择。从我国现在的国情看,我国有必要将财政纪律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正常环境下的财政纪律,严格自我约束;另一种是危机时期的财政纪律,先活着再应对副作用;第三种是介于两种状态之间的转型和战略改革阶段。国际上财政负担的上升,往往是在面对特定要求后阶梯式上升的。我国应重新评估财政支出的合理约束。
另一方面,当前已出现经济边际变弱的迹象,金融风险暴露的压力仍较大,与美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不同步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变动,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明年的经济政策,可能需要考虑采取“双松”的组合。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陈道富,本文是在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月度研判例会上的发言。)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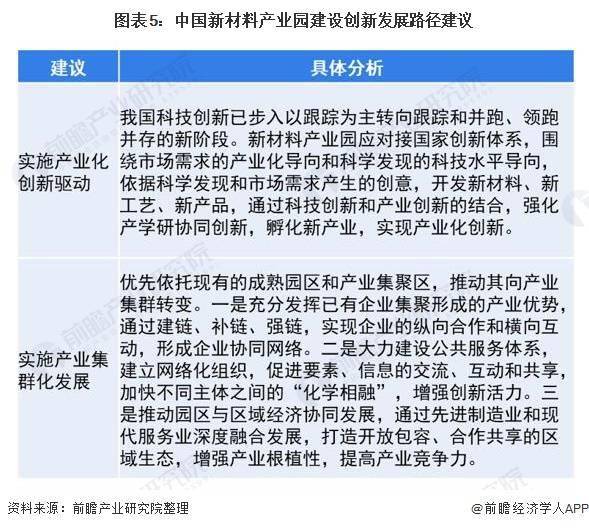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