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康淋是四川省蒲江县西来九年制学校的校长。在这所有923名学生的学校里,留守儿童的比例为38.5%。赵康淋在做了一番调查和研究后,认为“留守儿童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
赵康淋调查的数据显示:一至六年级的留守儿童群体中,很多学生的父母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3次,甚至个别父母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其中,有两成的留守儿童每月和父母的通话不超过3次。
通过分析一至九年级近两年来的期末考试成绩,他发现,成绩靠后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都是留守儿童。赵康淋还梳理了全校学生的违纪情况,其中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经常抽烟、喝酒、打架、旷课的学生里,有很多是留守儿童。
在和学生的相处中,赵康淋发现,留守儿童在应对压力时会出现更多的退避,做事任性、对人冷漠、性格内向和孤独等都是他们的突出特征。
在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善槐看来,留守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违背价值标准或者道德认知范围内的各种反应和表现,可以理解为越轨行为。
在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调查和分析后,刘善槐认为越轨行为有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消极行为,包括对亲情的漠视,表现出不依赖父母或者厌烦父母;二是回避人际活动,孤僻、不自信、不合群;第三个层面则比较严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轻生和厌世。
“留守儿童只是一个特殊群体,并不是问题群体。”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杨清溪在论坛上提出,要避免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矫往过正倾向。
“不要让留守儿童变成一个负面标签。”杨清溪担忧的是,如果从问题导向来教育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就会给人以“弱势群体”“问题儿童”等负面印象,“一旦被贴上不良标签,就可能导致不良行为的发生”。
在杨清溪看来,以学校作为教育主体,联合社会多方力量帮助和引导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才是教育他们的关键。
杨清溪的呼吁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铁芳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当下开放多元的现代化环境中,乡村教育和乡村儿童都面临着边缘化处境。长期关注乡村教育的刘铁芳指出,这种边缘化处境最伤害孩子的心灵。
“留守儿童成长的核心问题就是从小缺失爱、安全感匮乏和交流有阻隔。”刘铁芳说,他们更多地沉迷于网络,缺少现实交流,难以向社会和他人敞开内心。
“帮助乡村儿童找到自我认同,是救援和守护他们心灵的钥匙。”刘铁芳认为,“爱和艺术可以帮助孩子们发现和认识自我。”
刘铁芳认识一位去云南支教的老师。这位老师刚去时,发现优等生只是少数,很多孩子选择用打架和早恋的方式来宣泄自我。有一天上课,大雨打到玻璃窗上,孩子们不约而同地看过去。这位老师突然有了想法,大家喜欢看雨,那就听雨声来写诗。
一个孩子的诗让刘铁芳触动颇深——“我是一个自私的孩子,我希望世界上有个角落能在我伤心时空着安慰我,我是个自私的孩子,我希望妈妈的爱只属于我一个人,让我享受爱的味道。”
“很多时候乡村教师的专业情意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刘铁芳认为,爱与关怀能让留守儿童生活在爱中,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审美和趣味,激活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除此之外,乡村教师要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承认和激励。
留守儿童主要分布于乡村学校和寄宿制学校里。在刘善槐看来,家庭教育缺失而完全依靠学校和教师,很难保证留守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
“父母不在家,并不意味着就可以缺失监管和责任。”刘善槐建议,通过制订详细的网络监督计划,部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学校可以定期召开网络家长会,设立留守儿童和父母的网上聊天室。社区也可以建立留守儿童活动中心。通过家长、学校和社区的三方联合,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成长。
此外,学校还可以尝试建立大学生志愿者与乡村儿童的一对一帮扶。刘善槐说,通过与学校对接的大学生志愿者视频见面,乡村儿童可以找到值得信赖的倾诉对象,排除生活和学习的烦恼,明确成长方向。
“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农村社区教育功能到了迫切需要加强和完善的地步。”赵康淋建议,由基层教育部门牵头,联合共青团、妇联和工会等组织,共同建立农村中小学生的社会化教育和监督体系。
父母缺位,留守儿童心灵的健康成长更需社会的参与。参会的教育者们期待:在留守儿童的成长中,可以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生命有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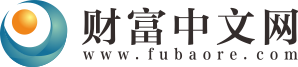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