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永伟/文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为两位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这届诺奖可谓是看点颇多。不仅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夫妻双双获奖足以大抓人们的眼球,迪弗洛以47岁的年龄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也颇具话题性。而除了这些八卦之外,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是备受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为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迪弗洛:诺奖夫妻档
阿比吉特·巴纳吉于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虽然巴纳吉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苦出身,但他却是从小就见过穷人们“摇摇欲坠的房子”的。小时候的他经常和穷人家的孩子玩耍,也经常输掉自己口袋里的玻璃弹珠。由于这些近距离的接触,他很早就是一个贫困人群的同情者。大学时,巴纳吉就读于加尔各答大学,这也是他父亲任教,并且担任经济系主任的地方。1981年,他从加尔各答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进入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继续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后,他又远赴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之后,巴纳吉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并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现在,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计量经济学会会士,并担任印度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顾问。
在攻读博士期间,巴纳吉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在经济学界,马斯金可谓是大名鼎鼎。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的专家,并因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知名度很大程度还要源于他的中国弟子们——清华大学的前任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重恩,苏世民书院前院长李稻葵,还有著名经济学家许成钢都曾是他门下的弟子。
作为马斯金的高徒,巴纳吉早年的研究路子是很理论化的。在这一时期,他曾经发表过不少纯理论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曾在1992年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发表过一篇用博弈论分析“羊群效应”的论文,这篇论文至今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钻研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尝试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不过,对于所有的这些问题,巴纳吉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理论性的。直到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太太迪弗洛开始合作,巴纳吉才逐渐开始将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了随机控制实验,并将自己的研究场所从安静的象牙塔转回到了自己童年时就曾经熟悉的贫民窟。有人说,如果发现一个男人突然成长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命中的那个女人。这句话放在巴纳吉的身上,恐怕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个巴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艾斯特·迪弗洛于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一位数学教授,母亲是一位儿科医生。在迪弗洛幼年时,她的母亲经常参与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计划,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冥冥之中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本科时期,迪弗洛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最初,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远赴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调研。在那儿,她遇到了当时正在为俄罗斯政府担任顾问的“休克疗法之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撬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要在满足自己学术理想的同时,又能真正有所作为,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迪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1994年,她从巴黎高师毕业后,就进入了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也就是现在的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巴纳吉。在巴纳吉的关照之下,迪弗洛的学业很顺利。1999年,她拿到了博士学位,并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按照惯例,美国的高校一般很少直接留用自己的毕业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巴纳吉帮的忙,但我宁愿相信这是迪弗洛自己的实力使然——不要说巴纳吉当年有没有这个意愿,即使想,以他当时的资历也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留下迪弗洛是非常明智的决策。通过和巴纳吉等合作者的合作,迪弗洛学术成果卓著。凭借这些结果,她仅仅用了三年就获得了终身教职——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的获得可能要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2010年,迪弗洛年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界,克拉克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只奖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中有一大批都在日后获得了诺奖。
现在已经很难考证巴纳吉和迪弗洛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2012年。由于种姓的约束,巴纳吉并没有马上和自己的原配夫人离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离婚,并迎娶了迪弗洛。由于两人曾经是师生关系,并且还夹杂了婚外情的桥段,所以很多人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这段婚姻颇为诟病。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人传出恋情,事实上已经是迪弗洛毕业后多年的事情,因此这段恋情严格意义上并不算什么师生恋。此外,如果从两人对彼此的学术影响和帮助来看,我个人倒认为迪弗洛对她原本的导师巴纳吉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巴纳吉原本的学术传统来自于马斯金,是习惯于用理论来分析问题的。作为导师,他指导迪弗洛的也是这个套路。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两人的发表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的最初,两人合作的文章都是理论化的,而与此同时,迪弗洛却已经开始独立应用实验的方法研究问题。根据这点,我认为迪弗洛对于实验方面的开拓应该不是受巴纳吉影响所致,对她在这方面造成影响的可能是其博士期间的另一个导师乔舒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然而她又转手用这些影响了巴纳吉。从这个角度看,迪弗洛并不是巴纳吉阴影下的弱女子,相反,她应该是帮助巴纳吉走向成功的女人。
克雷默:寻找O环的人
与前两位诺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生于1964年,本科和博士都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不久后就回到哈佛任教,一直至今。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的“发展中社会盖茨讲席教授”(Gates Professor of Developing Societies),同时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雷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以来一直是诺奖的大热门。恐怕很少会有人想到,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他的学生却抢了先,不知道巴罗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时作何感想。
受巴罗的影响,克雷默早期的学术研究都是比较宏观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领域。1993年,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环理论》。这篇论文的视角非常宏观,分析工具则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和他后来斩获诺奖的工作完全不相干。不过,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事实上奠定了克雷默后续工作的精神基础。
什么叫O环呢?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克雷默借用了这个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在了自己的理论中。
在论文中,克雷默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实是要有大量不同人员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对于每一个生产的参与者来说,他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完成任务,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取决于其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好像要让一个航天器成功发射,光有动力系统、控制系统还不够,O环的质量也可能造成关键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尽可能选择和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来合作,每一家高生产力的企业也都会尽可能选择那些高生产力企业扎堆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高能力者与低能力者,高生产率企业与低生产率企业的彼此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些关键的发展环节上存在着瑕疵,那么它就很可能难以吸引到高质量的发展资源,从而陷入不发达的陷阱。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讲,就是细节有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雷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路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自己学术传统的背叛,但仔细想来,他其实一直秉承了自己的初心。是的,既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成败可能被一个像O环那么小的东西所影响,那么如果可以找出这个O环,把它的质量搞好,不就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落后,帮助穷人走出贫穷了吗?本着这一理想,克雷默开始借助随机控制实验来找寻这些O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2005年时,杰弗里·萨克斯——对,就是建议迪弗洛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的那位——出版了一部新书《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在书中,他向全世界宣告: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得到解决。根据萨克斯的估计,如果从2005年到2025年间,富裕国家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来对穷国进行援助,那么到2025年时,贫困问题将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言信心满满,但这一观点一经发布,就有很多学者表示了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的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事例表明,尽管富国劳命伤财地对穷国提供援助,但这些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弭贫困的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援助反而让穷人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事例整理成了一本书,并特意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在另一本名为《援助的死亡》(Dead Aid)畅销书中,曾供职于高盛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也表达了和伊斯特利类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但会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会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因此它们经常不能达到本来的目的。
作为顶尖的学者,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尽管争锋相对,但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显露出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发现这门学科基本是无所不包的:资本如何积累、人力资源如何开发、工业化与农业化如何进行、人口在部门间如何流动、对外贸易如何开展到国外资源如何利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制定、计划与市场如何协调、发展的优先顺序如何选择……所有的这一切,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在早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很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74年获奖的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9年获奖的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都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 “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层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以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说RCT。
经济学家的实验室
至少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开始,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依照物理学为模板来塑造自己的学科,试图把自己从一门学科变成一门科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科学,它一方面需要理论的创造,另一方面还需要有实验的支撑。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是成功的。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发展,主流的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严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包装,这让经济学至少在外表上已经有了足以与物理学抗衡的理论形态。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脚步却略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更遑论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人却是活的,他们的反应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而对他们的控制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实验,用来验证我们熟悉的供给需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就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的实验十分简单,能用来分析的问题也十分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借助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的行为。由此,经济学家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毕竟不是人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反应。它们究竟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有意义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就要直接把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这种实验的逻辑,是借助于一些外生的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来对它们的表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最低工资法的效应争议不断,有的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就把最低工资法贬的一无是处,认为这会有损就业,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杀去世的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 Krueger)曾经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动作为冲击,比较了这一冲击发生前后,新泽西州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的RCT。严格地说,自然实验只是一种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对实验的模拟,而没法像真正的实验一样去对各种外生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而RCT则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为了完成对实验的控制,实验者必须真实地为被试提供相应的激励。例如,如果要分析补贴对疫苗注射的影响,实验者就需要真实地对一部分被试者提供资金补贴,让他们作为控制组,来观察其反应。而其他的被试者,则应该被视为对照组,用他们来和控制组进行比较。严格地来看,当实验者进行这一切时,他们不应该让被试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应该知道自己是实验者。
从理论上讲,由于田野RCT的环境比实验室实验更为真实,因此可以比后者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情形。同时,比起自然实验,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点,田野RCT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研究的标配。
探索贫穷的本质
拜RCT这个分析工具,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这批新的发展经济学家终于可以一改前辈们指点江山的风格,转而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去观察穷人,以探索贫穷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应对之策。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时候,看似难以根治的贫困问题其实只是由一些很小的问题造成的,只要对应地在这些问题上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激励(或者用理查德·塞勒的语言,叫进行一些“助推”(nudge)),就有可能帮助穷人摆脱贫穷的困扰。
以教育问题为例。所谓“扶贫必扶智”,很多地区的贫穷落后,本质上都是由于教育落后所导致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配置这些资源就是改善教育质量,进而帮助本地人民脱贫的重要举措。但是,究竟应该把这些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呢?一些观点认为,要用来给学生买课本;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学生的午餐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尼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免费午餐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课本也仅仅只对最优秀的学生有效。由此可见,这两个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质量的良方。
当然,教育资源的稀缺并不是教育的唯一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师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一旦教学内容适应了学生需求,教学效果便会明显提升。为了验证这一点,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两个印度城市——孟买和瓦都达拉进行了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了几所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针对性辅导,并将教学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针对性辅导均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师的缺勤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原因。为了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三位诺奖得主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缩短教师的合约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师的紧迫性,从而让他们的缺勤显著下降,而这对于提升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效果。
再看健康问题。在很多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导致疾病的众多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穷人们出于预防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了不预防、不治疗。
在克雷默所有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关于药物价格对患者服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影响的。借助RCT发现,如果驱虫药是免费的,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也骤降至18%。这说明,穷人们大多对价格十分敏感。而从政府的角度讲,对于治疗关键疾病的药品,可能只要进行一点点的补贴,就可以改变穷人有病不治的行为。
除了价格以外,低劣的服务质量也会影响穷人对于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区,尽管有疫苗接种站,但工作人员经常脱岗,这不但导致贫困地区的人们经常不能接受接种服务,也很难对疫苗的可靠产生信任。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班纳吉和迪弗洛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将接种站在随机选定的村子中流动,并确保接种站中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岗。结果发现,服务质量改善后,疫苗接种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6%增长到18%。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奖励对于接种的效果,对完成接种的居民奖励一包扁豆。结果,居民的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了39%。
通过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借助RCT的方法,研究者可以有效地发现很多原本被忽视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正如挑战者号上的O环,只要花点资源,保证这些O环的质量,就可以对有效缓解贫困问题。
除了探索贫困的本质外,RCT还有助于反思一些扶贫政策的得失。限于篇幅,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关于小额信贷的。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难以获得信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贫困,就必须鼓励金融机构为穷人贷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实践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对于这一看似显然的常识,巴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质疑。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仅很难达到像尤努斯宣称的那样高的还款率,它们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显然,这一发现让促使人们反思小额信贷的成败是大有启发的。
另一个例子是化肥的使用。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因此很多国家都利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但在实践当中,这些鼓励政策的成效却往往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过RCT实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农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于一种“现时偏差”(present bias)——既然关于化肥的补贴是长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风险,那么何不让别人试试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农民都这么想,那么化肥就很难推广开。针对这一问题,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议,应当将长期的补贴改成短期补贴。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对农民更为苛刻了,但从实践效果看,却是改善了农民的福利。
尽管每一年的诺奖都会引发一些争议,但似乎都没有今年这么大。事实上,在今年的诺奖公布之后,就有很多学者出来说,今年的几位得主根本不配诺奖。考察这些反对的原因,除了少数是针对得主本人(例如针对巴纳吉和迪弗洛的师生恋)外,更多的质疑是针对RCT这种方法的。
事实上,在经济学界,RCT这种方法一直存在争议。很早的时候,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就专门写文批评过RCT,由此还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论战。
那么,RCT方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教授曾经有一个比较到位的评论。在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教授指出,RCT这种试图“以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政策来减贫”的方法尽管对于理解一些特定的微观发展项目颇有帮助,但它们通常并不是以如何填补我们最紧迫需要了解的知识空白为目的来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它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以那些容易看到的话题为对象,对于政策制定的正面影响往往是研究过程中偶尔迸发的无心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林教授对RCT的看法,那就是它只能解决小问题,却解决不了大问题。
林教授的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从现有的RCT实验来看,它们解决的只是类似寻找O环的工作,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这就好像,虽然没有O环不行,但有了O环,没有助推装置,飞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样。在现实中,那些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简单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举例来说,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但究竟产业政策的效应如何、究竟是否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又是否会衍生出各种其他的问题,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定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前几年我国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林毅夫、张维迎、田国强为代表的众多著名经济学家各执己见,争论得不亦乐乎。但怎么判断这几种观点的正误呢?记得当时有一个讨论群里,有群友提议“干脆做个RCT,让东北三个省,分别按照林、张、田三人的思路去发展,过几年看看谁发展得好!”这个观点引发的只是一阵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的大事断然不可能用实验来解决。
除了林老师指出的上述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结论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毕竟是实验,换个场景,换个更大的环境,这些结论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难说。就以前面的产业政策问题为例,即使政府真的采纳群友的建议,用三个省来做实验,但从省级得出的经验真的能推广到全国吗?恐怕还是很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T其实也不便宜。我曾在聊天的时候问过一位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RCT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什么?她的回答是:“在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当然知道她是在调侃,但这个回答其实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耗资十分巨大。尽管相对于政策的实践来说,实验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实验的成本却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巴纳吉、迪弗洛他们所做的那种实验,即使在操作上简单得多的RCT实验也可以轻松耗去上百万的经费,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显然难以完成。由于耗资巨大,要重复RCT实验就很难,人们因此也很难知道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当然,RCT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只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涉及贫困的面上问题,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则需要更为直接的倾听与调查。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贫困的成因是复杂的,为了根治贫困,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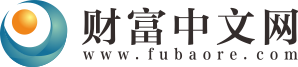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